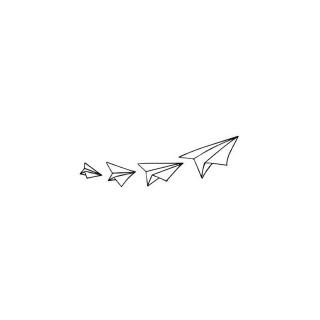
介绍:
约莫是七八岁光景,对门的年轻嫂子出了车祸,本家的哥哥哭了一夜,把媳妇儿照片摆在堂屋正当间儿。看着三个不懂事的娃娃,抽了一宿的烟,嫂子生前最讨厌他沾酒抽烟,如今痛饮到半夜,也再无人过问了。
小时候,人生得有点钝,记忆总是有点模糊,只隐约明白在一片片耀眼的红色里有了新嫂子,与我同龄的侄子侄女有了新妈。新嫂子人生得黑,眼睛倒是挺大,头上插了劣质塑料勾连出的假花,脸上没有笑。
哥哥不说一句话,对旁人的起哄木呆呆无应答,这场婚礼办得索然无味,哥哥的妈却流下了泪。过了世的嫂子叫青竹,身姿气度像极了竹子,哥哥敬她爱她,即使嫂子脾气来得急躁,哥哥也笑得狡黠。
新嫂子褪去腼腆,渐渐变得熟稔起来,哥哥固执地摆着青竹嫂子的牌位,过节时对着牌位喝一场酒,抽几包烟。
新嫂子赌气出了门儿,侄子喊了我们尾随,一伙半大孩子(侄子好像有9岁?)自以为掌握了跟踪别人的技巧,在新嫂子身后悄没声儿地意淫着自己跟踪术的高超。
小路两旁记得种的是麦子,绿得发黑,正午阳光下尤其亮。新嫂子回头看时,大家卧倒在麦子里,如是再三,现今想起来,咧嘴大笑,侄子跳起来趴下去划出的线尤其让人捧腹……
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看到一个红砖堆砌的高高的烟囱,新嫂子顺着倒人字形的一撇拐了进去。大家伙儿没了主意,我们固执地认为她没发现尾随者们,如果贸然走进去无疑是暴露了自己,最后考虑到日头渐西,才磨磨蹭蹭进了去。
新嫂子躲在墙根儿,胳膊搂着两条腿,戚戚切切地对着麦子哭着喊着。麦子在风里油油地晃着,新嫂子在麦子对面把头埋进腿里。我们后来怎么回去的倒是忘了,只是隐约记得有些颓丧,好像在成人世界里窥探到了什么,却始终说不出来。那条路上的夜色和白杨,常常浮现在脑子里,丢不开。
后来新嫂子不新了,侄子侄女也都结了婚有了孩子,新嫂子带来的闺女也嫁得不错。在妈妈们的悄声低语里,我细心地为嫂子的故事添着枝叶。
新嫂子做姑娘时,认识了一个男人,轰轰烈烈投了进去,怀上了孩子。男人反悔,新嫂子一家蒙羞,赶上我哥哥娶续弦,慌不迭地给推了出来。
怨天尤人抵不过时日对人心的消磨,老来有伴抵得过年青时的一往情切?不懂,不通,不了解。
麦子灌浆时,农人总怕落雨一场,沾了雨水的麦子能得了清香几许?
惟盼望一场烈日,几分骄阳。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