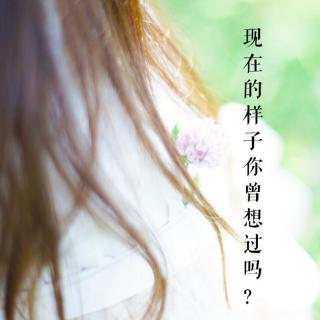
介绍:
作者:忘川里拾起了夏(微博@忘川里拾起了夏)
背景音乐:1.甘仕良 - 还是觉得你最好;2.赵海洋 - 最美的时光;3.赵海洋 - 北京北京;4.王崴 - 被遗忘的时光
我在七点整的时候按下了发送键,那时候还不习惯语音,简简单单的一句生日快乐,随后阿东的头像闪了闪,惠灵顿比中国快5个小时,信息的送达,是在他那边的午夜。
他没想到在大洋的彼岸会有人记得他的生日,我没想到在不同的时差下他还能秒回我。
刚开始流行微信的时候,以前的同学都渐渐起了联系,大家建了群聊,虽到了不同的地方,仍是很怀念初中时的那段时光,都是以年为量的感情,重到难以割舍。
阿东是个例外,我们认识的时间远不止这短短的初中三年,从小学算起,直到那天生日,是真的十年之交。
那一年我们中考落榜,他报了IT国外班,我则打算回老家复读,没打任何的招呼,他打电话约我出去最后一聚的时候,我已经隐约能看到爷爷家的轮廓了。
那一声有缘再会,成了一段电话录音。
毕业那天,我试着点开qq里那个一直灰色的头像,这是我们年少时的联系方式,也是这么多年后仅存的最后一种联系方式,在他生日那天,祝他生日快乐。
“有段时间我登了号,看着你写的东西,我真是不敢相信,你真的变了好多,十年前的我根本想不到,如今的你居然在写文章。”他唏嘘不已。
“哈哈,我也没想到,当年英语考试总是二十来分的你后来居然毅然决然地出了国。”我打着开心的语句,鼻子却莫名的一酸,视线有些模糊。
语言不通,一个人漂洋过海,我就算不用脑子都知道这些年他是怎么过的。
如果能够再来一次,那十年,你说我们会不会收敛一些,老老实实当一个认真读书的乖孩子,不去网吧,放学后不在大街小巷胡闹,不再旷课,按部就班地走下去。
我笑他又在犯矫情,他打个哈哈,说他只是开玩笑。
却是在下一秒钟,同时敲下了两个字。
不会。
现在的你,以前有没有想过是这个样子?阿东问。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却在那个晚上,喉咙一哽,哭得稀里哗啦。
从没想过自己长大会是什么样子啊,一步步走着,后来你累了,回过头看看,才发现,原来已经走了好远好远,你再也看不见那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跟你挥手,远到途经的风景随着年月绿了又青,毫无顾虑地往前走,从来不曾想过未来会怎样,直到有一天,你突然想跟大家说声谢谢,转过身才发现。
一路走来,随了你一程的,只剩下自己的脚印。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写故事,奶奶笑着说她的孙子以后要当小作家。我望着奶奶傻笑,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一年我八岁,没想过以后会怎样,看着奶奶笑,我就觉得好开心。
小学时,起了懵懵懂懂的情愫,喜欢了班里的一个女孩,暗恋总是不朽的题材,那时候的我,莫名地爱上了诗歌,喜欢泰戈尔,北岛,日记本里满满的情诗,一些稚嫩的情话。那时候的孩子很难有秘密,母亲将我的小本子翻出来,虽没说什么,但也是在和父亲讨论,我躲在房里,面红耳赤,找出余下的本子整理好,将那些年的暗恋,偷偷丢进了垃圾桶。
那一年我11岁,没想过以后会怎样,就只是觉得能把自己说不出来的东西写在纸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不敢再写东西,变得沉默寡言,房间门开着时总是害怕后面有人看着,于是我放学后喜欢在小区楼下坐着玩,那里有块沙地,我捡根小树枝在上面写着那些转瞬即逝的诗,写了擦,擦了再写,一笔一划,想到什么写什么就已经觉得很开心。
初三那年,我在书店逛着,第一次看到小四的书,拿着那本《左手倒影,右手年华》,讶于他笔下的人物骨子里的那份随性和多愁善感,在那样的岁月里,我爱上了《夏至未至》里的立夏,羡慕着傅小司的人生,那时候我总背着个包包,在书城的阅读区写随笔,于风,于景,于人,是我眼中最美丽的山川河流。
那一年我15岁,没想过以后会怎样,只是突然觉得,身边有一个本子,一支笔,原来是这么幸福的事,走走停停,将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看着生活一天天改变,而时光曾在你的笔尖划过,你跟它挥挥手,它向你点点头,这就很好。
高中时,离开了父母,到了另一个城市生活,因为复读考上来的,同届的朋友都成了学长学姐,早就没了那种新学年该有的感觉,那时候的我总觉得自己跟周遭格格不入,没有喜欢的明星,没有特别大的野心,也没有那种为班级争光的干劲,一个人走在校园里,格外的喜欢那份宁静安逸,我开始喜欢上了散文,余秋雨,张爱玲,梁秋实,一页页地翻着,看得入了迷。
那一年我17岁,没想过以后会怎样,在那个张狂的年代里,我趴在课桌上打盹,纸上的笔迹未干,勾勾转转,续着岁月里特有的绵软悠长。
当了两年历史科代,任课老师是个很淡雅的女人,做事不温不火,不急不躁。她能跟我讲很多书本上所没有的东西,我讨厌死气沉沉的课堂,却特别喜欢看史家杂记,她鼓励我去研究,去写作,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真的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不是大家眼中的怪人。
那天我回家,看见那串起了锈的钥匙,想起了那三年陪伴我的书柜,午后的阳光挺好,我打开了房门。
书柜里角挂着些许蛛丝,一圈绕一圈的,扑上高高的架台。
翻开那些绵实的封袋,意外地找到了那纸略显苍劲的手笔。
“一下笔,就是整个春秋,一辈子,就落得了几页纸,你读的东西啊,是一生,是细水长流。”
那时候我喜欢去图书馆读史,推着眼镜将列传翻得哗啦响,一目十行,平淡无奇的内容让我困得想睡觉,有个小哥经过我身边,拔开笔盖,在我的本子上留下了这句话。
我撑起脑袋,望着他的脸。
他举着手里的林徽因传,对着我笑了笑。
“落梅风骨,秋水文章。”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对白落梅的一句评价这么在意,后来当我自己看了一遍林徽因的传记后才明白,他在意的不是这个名号,而是这个名号笔下所带给他的感触。
我始终不知道他的名字,却是感谢在那个细碎的午后,他教给我的那一纸情愁。
14年的晚修,我读完了庆山新作下的那位厨子,这是安妮宝贝改名后的第一个故事,也是我那一年看的最后一个故事。
后面的三章我一直没舍得看,放好书签后,连着那纸墨迹封的严实,置于架子的最顶层。
将门把反锁,便再也没人碰过。
那里有着很多让我走到现在的东西,有三毛和她的荷西,有顾城,有北岛,有仓央嘉措,有沈从文,有我这些年的矫情造作。
那里有蛛丝,有笔墨笔记,有尘埃,有我褪下的阳光,有着好几段春秋。
物是人非,细水长流。
一转身,就是过往的少年。
再过多几个星期,我该20岁了,没想过以后会怎么样,8岁那年,我没想过自己会写到现在,11岁那年,我没想过会有一天,我写的东西能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而不是在沙池或是垃圾桶,15岁,17岁,我什么都没想过。
我从来不是个身带光环的人,不被人看好,中考落榜复读,上了个半吊子的高中,高考考得不尽人意,也没上什么排的上号的大学,甚至连本科都不是,一直以来没干过什么让父母亲值得骄傲的事,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辉煌。也从来没有什么比较远大的理想,真要说有的话,也许就是奶奶的那句,当个小作家了吧。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在沙地里写诗歌的自己,后来我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孤独无援,自己一个人撑下去,我总能想起那个在沙地上一笔一划地写诗,满心欢喜的孩子,然后我就想啊,可不能对不起他的努力,再怎么辛苦都要走下去,还是老规矩啊,不要想以后会怎样,至少现在没有后悔,那就足够了。
一路走来,其实你已经做的很好。
现在的你是自己曾想过的样子吗?
是的,这是我曾想过的样子。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