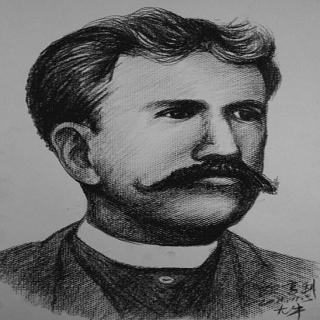
介绍:
已退休的老安东尼•洛克沃尔是洛氏尤雷卡肥皂的生产商和专利人。现在,他正在自己位于第五大道上的豪宅里,站在书房的窗口往外看,一边不由得咧嘴笑着。住在老安东尼豪宅右边的邻居——
一位贵族俱乐部的成员乔•范•斯凯莱特•萨福克•琼斯——
正从家里出来,走向等候着他的汽车,像往常一样,他冲着肥皂大厦正面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雕像,轻蔑地蹙了蹙鼻子。
“你这个无所事事、自以为是的倔老头儿!”这位前任肥皂大王在品头论足地自语道,“你要是不小心点儿,伊登博物馆迟早会把你这个思想僵化的老古董收进它的馆藏。明年夏天,我将把我的房子漆成红、白、蓝三色,到时候,看你这个荷兰人的鼻子还能翘多高。”
临了,安东尼•洛克沃尔(他从来不喜欢按门铃)走到书房的门口,大声喊着:“迈克!”那嗓门一如当年响彻堪萨斯大草原苍穹时那般高亢。
“告诉少爷,”老安东尼对应声而来的仆人说,“叫他出去之前来我这里一趟。”
当小洛克沃尔来到书房的时候,老人放下了手中的报纸,抬眼看着儿子,光滑、红润的大脸盘上流露着严肃而又疼爱的神情。激动的老安东尼用一只手搔着他乱蓬蓬的白发,一只手摇动着口袋里的钥匙。
“理查德,我的儿子,”老安东尼说,“你用的肥皂是多少钱一块的?”
刚从大学毕业回到家中只有6个月的理查德,听到这话不免有些吃惊。他还没有能摸透老头子的脾气。他的这位父亲大人就像一个初次出来交际的姑娘,总会提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是六块钱一打的,父亲。”
“你穿的衣服呢?”
“我想,一般是在六十块钱左右吧。”
“你是个上等人,儿子。”老安东尼不容置疑地说,“我听说许多跟你一样的年轻人,用的是二十四块钱一打的肥皂,衣服往往是上百块钱一件的。你和他们一样有钱,完全可以像他们那样的挥霍。可是你没有,你只求适中就可以了。现在我用的仍然是我们老牌的尤雷卡肥皂,不仅是因为对它有感情了,还因为它的质地最纯。要是你买一毛多钱一块的,你买到的肯定是杂牌的,而且味道也不好闻。像你这样的身份和地位的年轻人,用五毛钱一块的,就蛮可以了。我刚才说你是个上等人。人们讲需要经过三代,才能造就一个上等人。他们错了,金钱就可以办得到,像肥皂的油脂那么顺滑地办到。金钱已经把你造就成了一个上等人。天哪!它几乎叫我也成了上等人。尽管我差不多跟作为我们邻居的那两个荷兰裔的老爷一样,粗鲁无礼,惹人讨厌,言谈举止也不文雅。”
“世上的有些事情是金钱办不到的,父亲。”小洛克沃尔的话里带着些许的忧伤。
“噢,孩子,不要这么说,”听到儿子讲出这种话,老安东尼有些吃惊,“我始终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我翻看百科全书,现在已经读到了以Y字母开头的内容,可还没有找到拿钱买不到的东西。下个星期我就读完它的附录了。我绝对相信金钱至上。你倒说说看,有什么是金钱不能买下的。”
“让我看,”理查德有些失望和伤心地说,“花钱也不能让人跻身于高高在上的社交圈子。”
“噢!有这样的事情吗?”这个万恶之源的拥护者暴躁地喊道,“请告诉我,如果阿斯特的老祖宗没有钱买三等舱船票来到美国,你所说的上流社会还会有吗?”
理查德叹了口气,没有吭声。
“这正是我打算要跟你谈的,”老人说,语调缓和下来,“这也正是我叫你到我这儿来的原因。你最近有点不大对劲了,孩子。我注意你已经有两个星期了。你有什么心事,就说出来吧。我想,除了咱们家经营的房地产,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还可以调动一千一百万美元的现金。如果是你的心呀,肝呀,出了什么毛病,逍遥者号船就停在海湾里,加足了煤,两天就可以抵达巴哈马群岛。”
“你猜得差不多,父亲。已经离得不远了。”
“啊,”安东尼急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
理查德开始在书房里来回地踱着步。他的这位看似粗鲁的父亲一下子就猜透了他的心思,这足以叫他对父亲产生信任了。
“你为什么不向她求婚?”老安东尼追问道,“她会巴不得扑进你的怀里。你有钱,相貌英俊,举止言谈又得体。你的手干干净净,从没沾上一丁点儿尤雷卡肥皂的味儿。你读过大学,不过,对这最后一点,她倒是不会看重的。”
“我没有这样的机会。”理查德回答。
“造一个出来嘛,”安东尼说,“邀她到公园里散散步,或者带她开车去兜兜风,或者在教堂做完礼拜后送她回家。哪里会没有机会!”
“你不大懂得像一个大磨坊一样的社会的运作,父亲。她就是叫那个磨坊转动起来的那股水流。她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都是在好几天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的。我一定要得到这个姑娘,父亲。否则的话,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永远是一片腐臭的沼泽地。我又不能写信表白——我不能那么做。”
“呸!”老人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有我这么多的钱财做后盾,你也不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跟这个姑娘单独地待上一会儿?”
“是我耽搁得太久了。她后天中午就要乘船去欧洲了,一待就是两年。明天傍晚,我能单独跟她待上几分钟。她现在是在拉奇蒙特她姨妈的家里。我不能到那里去看她。不过,她答应让我明天晚上八点半乘马车到中央火车站接她。然后,沿着百老汇街走一段,把她送到沃洛克剧院,她的母亲和别的亲友们都在剧院的休息室等着她。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境下,她会用只有七八分钟的时间,来听我诉说我的爱情吗?不会的。在剧院看戏时或是剧院散场后,我有机会吗?没有。不,父亲,你的金钱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我们不能用金钱买到一分钟的时间。如果可能的话,富人们的寿命就会很长久了。在兰特里小姐出国之前,我没有希望跟她好好地谈谈了。”
“好吧,理查德,我的孩子,”老安东尼喜形于色地说,“你现在可以离开到你的俱乐部去了。我很高兴,不是你的肝脏出了毛病。不过,你还是不要忘了时不时地到庙里去烧炷香,敬敬伟大的财神爷。你说金钱买不来时间?喔,当然啦,你不能用钱叫人把永恒打包好,送到你的府上。可是,我见过时间老人在走过金矿的时候,他的脚后跟被那里的矿石磕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那天晚上,正在老安东尼看报的时候,温柔体贴、多愁善感、满脸皱纹、被财富压得郁郁不乐、整日长吁短叹的埃伦姑妈(老安东尼的姐姐)来了,她跟老安东尼聊起了情人们会有的痛苦和哀怨。
“理查德把事情都告诉我了,”她的弟弟安东尼打着哈欠说,“我跟他说,我银行的钱全都听凭他的支配。他就开始奚落起金钱,说钱也帮不上忙,还说十个百万富翁加在一起,也不能把社会的规则挪动一步。”
“噢,安东尼,”埃伦姨妈叹着气说,“我希望你不要把钱看得太重了。在真情实感面前,财富真的就算不上什么了。只有爱情才有无穷的力量。要是我们的理查德早一点儿开口就好了!她是不会拒绝我们的理查德的。但是,现在恐怕是已经太晚了,理查德没有向她表白的机会了。你所有的金钱也不能给你的儿子带来幸福。”
第二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埃伦姑妈从一个被蛀虫啃蚀过的首饰盒里,取出一枚古色古香的戒指,交给了理查德。
“今天晚上戴上它吧,孩子,”姑妈恳求道,“这是你妈妈给我的。你妈妈说它能为爱情带来好运。她要我在你找到你的心上人的时候,将它转交给你。”
小洛克沃尔满怀着尊敬接过戒指,试着戴在他的小拇指上。戒指在滑到第二个关节的时候停住了。他把它摘了下来,照男人的习惯,放进了他的坎肩口袋里。接着,他打电话叫马车。
在火车站,小洛克沃尔从嘈杂的人群中于八点三十二分接到了兰特里小姐。
“我们可不能让妈妈和亲朋好友们久等。”兰特里小姐说。
“去沃拉克剧院,越快越好!”理查德顺从地说。
他们急速地驶过第四十二街,上了百老汇大街,然后,拐进一条灯火璀璨的巷子,从幽静的西区直奔高楼林立的东区。
到了第三十四街的时候,理查德推开了车窗,喊马车夫停上一下。
“我掉了一枚戒指,”他一边下车一边抱歉地说,“这戒指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我不愿意把它丢了。我耽搁不了一分钟的——我看到它落到什么地方了。”
没有一分钟,理查德拿着戒指回到了车子里。
但是,就是在那一分钟的时间里,一辆穿城而过的轿车径直停在了马车的前面。马车夫刚想着把车赶往左边,可是一辆满载的快运货车挡住了他。马车夫试着向右边赶,可却不得不又往后退,以避让一辆无缘无故出现在那里的装运家具的马车,谁知退路也被挡住了,马车夫只好丢下缰绳,无奈地诅咒着。他被横七竖八、里三层外三层的车辆和马匹围了个严严实实。
在这座大城市里,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道路堵塞,霎时间会中断了一切车辆的往来。
“为什么不赶路呀?”兰特里小姐有点着急了,“我们要迟到了。”
理查德在车子里站起来,向四下张望。他看到百老汇街、第六大道和第三十四街的各个宽阔的交叉路口被各色各样的货车、卡车、马车、搬运车挤得水泄不通,正像是一个腰围二十六英寸[31]的姑娘硬要束上一条二十二英寸的腰带一样。在所有交叉的道路上,还有车辆在轰隆隆地、加足马力地朝着这个交汇点赶来,把它们自己也抛入到这场拥挤当中,一时间轮毂交错,喧嚣声和司机、车夫的咒骂声此起彼伏。曼哈顿地区的整个交通似乎都因为这个地方的堵塞而变得瘫痪了。挤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人成千上万,也许他们中间年龄最长的纽约人也不曾见过有哪一次的交通阻塞,能与这一次的相比。
“真对不起,”理查德说着坐了下来,“看样子我们是动不了了。没有一个小时,这里的交通不可能疏通。这都怪我,如果我没有掉了戒指,我们——”
“让我看看你的戒指吧,”兰特里小姐说,“既然已经堵在这里,没有办法了,我们着急也没有用。其实,我觉得看戏也挺无趣的。”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