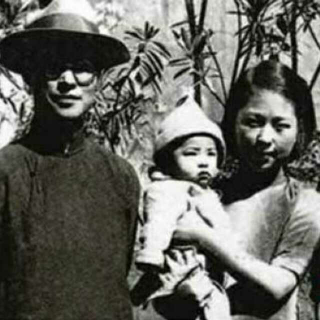
介绍:
可惜的是,婚姻除了写信和看信之外,还有太多实际的问题要解决。
回顾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生活,像上文中出现的甜蜜时光并不多见。和信中永存的爱情相比,他们的现实婚姻其实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矛盾重重。
他们婚姻中的首次危机出现在北京沦陷后。沈从文一路南逃,而张兆和带着孩子们留在了北京。两个人保持通信,这次不是说情话,而是在信中争执。沈从文想让张兆和南下,而张兆和则坚持留在北京,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沈从文的作品太多不方便带走。这些理由,说服不了读者,更说服不了沈从文,要知道,战火纷飞中,有什么比得上一家团聚更重要?当时文人大多举家南逃,留在孤城北京,换谁也不放心。到最后,沈从文火了,去信质问她:“你到底是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
这场争执,最后以兆和带着孩子南下告终,两人总算团聚了。但裂缝已经出现,并随着时间对婚姻的磨蚀而日渐扩大。
他们两个人原本就是不同的两类人,一个出身于湘西乡下,一个出生于合肥名门,性格、气质、爱好都迥异。以爱好来说,沈从文爱听傩戏,这种咿咿呀呀的野调在张兆和听来根本入不了耳,她爱听的是昆曲。沈从文喜欢收藏古董文物,张兆和对他这个爱好不以为然,说他是“打肿了脸充胖子”,“不是绅士冒充绅士”。沈从文爱结交朋友,有时也干些仗义疏财的事,张兆和整天都在为家里如何生活发愁,对此更是气恼不已。
写到这里,不禁有一个疑问,张兆和到底爱沈从文吗?我想,一开始是坚决不爱的,后来慢慢被他打动了,嫁给他后,应该还是爱他的。兆和性格本就冷静理性,她对沈从文的爱,更多的是在尽做妻子的本分,始终少了一点激情。她对婚姻的期待也同样务实,不过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不要太拮据,也不需要什么浪漫。
这本来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她嫁的人是沈从文。沈从文一身的诗人气质,对爱情、对婚姻有着更多的憧憬,他期望婚姻在相濡以沫之外,还能有灵魂上的相知相惜,他当然不满足于婚姻中仅仅只有平淡的亲情。
所以,当张兆和在为柴米油盐之类的问题指责他时,他仍然沉迷在感情生活之中。他们这个时期的信完全是鸡同鸭讲:一个抱怨钱不够用,一个指责她不够爱他。对于这段婚姻,他们投入的感情不对等,期望值也不一样。
从张兆和的表现来看,她的确是不够爱他的。她连他写的故事也不喜欢读,挑剔他信中的错别字,她甚至对他的稿子看不过眼,忍不住去改动里面的语法。殊不知,沈从文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文中的野趣,她对他,始终是不欣赏的。
沈从文呢,与其说爱张兆和,不如说爱的是心目中向往的一个幻影。婚后,三三成了他小说中一系列人物的原型,比如说《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还有《三三》中的三三,都是皮肤黑黑的,活泼俏丽,小兽一样充满生命力的女子。把张兆和与小说中的女孩子一对比,就会发现,她们其实只是形似而已,兆和为人太过务实,身上缺乏翠翠们生命的热度,没有那种爱起来不管不顾的劲儿。
对婚姻的失望一度曾让沈从文在婚姻外寻找安慰。
让他动心的那个人叫高青子,一个喜欢写小说的文艺女青年,对沈从文充满了崇拜。她在沈从文的老乡熊希龄家里做家庭教师,两人得以相识。一次,沈从文去熊家,高青子特意穿了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还在衣角袖口染了一点紫,这样的打扮是脱胎于沈从文一篇小说中的女主角。她的聪慧深深触动了沈从文。
沈从文坦承,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他对这段情史也并没有刻意隐瞒。那段时间,他常常出入“太太的客厅”,还特意为此跑去向林徽因倾诉,后者开导他说,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学着自己慢慢去化解。
张兆和对此很生气,为了挽回他们的婚姻,亲友们甚至给高青子介绍过对象。半个世纪之后,她提起来还耿耿于怀,不过她很公道地评价说,高青子长得很美。
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创作同名小说《主妇》,借此书对妻子忏悔,他在书中说 “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
可能很多人都会因此指责沈从文是渣男,我只想说,在漫长的婚姻过程中,厌倦、争吵甚至出轨都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如果单以一次出轨来论人品,那未免把人性想得太单纯了。
这次出轨事件只是他们数十年婚姻中的一次考验,更多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进入新时代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沈从文是顽固的理想主义者,美是他的宗教,除此外他并无信仰,也绝不愿意抛弃自己信仰了小半生的东西;张兆和则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属于那种适应性强、弹性较大的人。当她穿着列宁服,积极向新时代靠拢时,他却停滞不前,拒绝接受变化。
以前,他还可以遁入创作之中,可那时,他的作品被批评为“桃红色文艺”,而根正苗红的作品都要为新社会唱颂歌。既然不能再为自己写作,不能再用他觉得有意义的方式写作,那他宁愿搁笔。这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为自己选择的抗争方式。他总是那么顽固,顽固地忠于自己的心。
没有人理解他的顽固,包括他的家人。那段时间,沈从文孤立无援,被大学生贴大字报,被老友们孤立,被发配去扫女厕所,因为抑郁症一度住进了精神病院。张兆和却适应得很好,后来还当上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她和两个儿子都无法理解沈从文,他的儿子回忆说:“(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有那么几年,沈从文和家里人分居两室。每天晚上,他到张兆和那里去吃晚饭,然后带回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去住处吃。那几年的冬天,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天了吧,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他开始将精力从写作转移到学术上,一个人就着冷饭馒头,埋头进行学术研究。他的家就在咫尺之外,究竟是什么让他不愿意回家?
这个时候,他是否会想起胡适当年所说的话,“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用错情了。”
即使是在生命中最灰暗的时期,他仍然坚持给她写信,写给他心中的幻影,他的三三、小妈妈、小圣母,他的乌金墨玉之宝。不管她爱不爱看,能不能理解,他只顾写,他在信中说:“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这样的字句,令人不忍猝读。他并不盼望她的来信,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已经得到安慰。
关于信的故事,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底一封信》里提到:“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那一刻,他怀念的不是相伴了数十年的妻子,而是多年前提笔给他回信,又温柔又调皮的那个三三。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致力于整理出版他的遗作。在1995年出版的《从文家书》后记里,她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她不是不爱他,她只是忘了去懂他。等到终于懂得的时候,他已经离她而去。
一切都太晚了,几年后,张兆和因病逝世,死前已认不出沈从文的画像。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