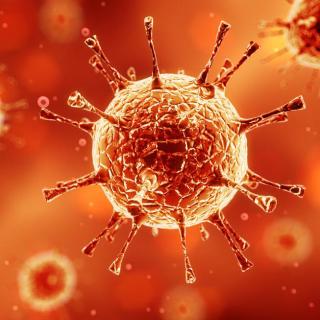
介绍:
幼儿园里,孩子们在打打闹闹。只有两岁的马丁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哇地哭了起来。马丁觉得她哭得莫名其妙,去抓她的手,想安慰她,但她哭着躲开了,马丁轻轻拍了一下她的手臂,好像是在向她表达歉意。
小女孩不领情还在哭,马丁生气了,把脸转过去不看她,大声说:“不许哭!不许哭!”声音一次比一次急促,一次比一次响亮。
马丁想再拍她,她又一次反抗了。这时马丁愤怒了,好像咆哮的小狗那样露出牙齿,吓唬小女孩。
马丁再一次开始拍打小女孩的背部,不过拍打很快变成了捶打,马丁不管小女孩可怜的尖叫,一直重重地打她。
小女孩刚开始的哭,让马丁意识到他的不小心可能把小女孩给碰疼了。他油然升起一种怜悯和歉疚之情,但他同时又觉得小女孩哭得有点夸张,甚至有点刻意,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当履行了安慰表达了歉意之后,他认为自己该做的都做了,事情应该结束了,小女孩还不停止哭泣就是她的不对了,是在故意找茬了。于是,无声的安慰变成了凶狠的咆哮,轻轻的拍变成了重重的打。他等于是在拼尽全力去制止一个小小的哭泣。这样夸张的行为与他认为的小女孩的夸张的哭泣,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模仿关系。
两岁的马丁正处在无意模仿而又擅长模仿的年龄。他小小年龄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面对事情的态度和方式,那就是:一切从自我出发,以自我的感觉和判断为依据,用暴力解决问题。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多半是无意中模仿来的,而最可能的模仿对象是他的父母。
马丁以前也不可避免地多次哭泣过,他的父母对待他的哭泣的态度和方式多半也是先安慰继而暴力。小小的马丁当然分不清暴力的对错,他只是明显感受到了暴力的威力,结果就是他不敢哭了,暴力有效地终止了他的哭。这让他既恐惧暴力又迷恋暴力,或者说正因为恐惧所以迷恋。就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迷恋恐怖片,那原因就在于片子很恐怖。这些都是人们知道的东西,但暴力还有一个魅力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就是:暴力可以让受暴者成为施暴者,就像SARS、埃博拉、AIDS病毒一样,在摧毁健康细胞的同时,也在同化健康细胞,让健康细胞变成自己的同类。而暴力比SARS、埃博拉、AIDS更可怕的是,它是隐藏的不可消灭的病毒。
鲁迅在谈到国人的“凌虐”现象时,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鲁迅只是说“可以”一级一级地“臣”下去,也就是“凌虐”下去,也就等于说也可以不“臣”下去,不“凌虐”下去。但事实上为什么往往是“臣”下去,“凌虐”下去的呢?那原因大概就在于,暴力一旦发生,就会传递下去,扩散出去。暴力的“力”跟其他力一样,它是会被传递的。就像多米诺骨牌,推倒第一张后就可以袖手旁观了,第二张、第三张……一直到最后一张,皆顺次倒下。我们心里清楚地知道,它们都是被某个人推倒的,而它们都不知道,除了第一张牌,还以为是被前面的一张牌给推倒的;而第一张牌也可能会傻傻地以为是他不小心压倒了第二张牌。所以我们会偷着乐,所以会喜欢玩这个游戏。而当这个游戏不仅仅是个游戏,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情境的时候,我们可能想乐也乐不起来了。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