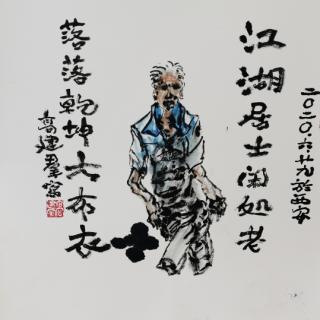
介绍:
陕北旧事——
担担匠
文/任静
担担匠,其实不是工匠,而是我的家乡给予挑箩担箱的货郎,一种极客气的尊称。
时常萦绕在我童年记忆中的始终是拨浪鼓清脆的声响,“哐啷”、“哐啷”,一阵阵拨浪鼓敲击所发出的清音,在有雾的早晨像阳光一样响亮地响起来,轻轻撩拨开我记忆中最纯、最美、最真的一段童年时光。
先是听到“哐啷”、“哐啷”的鼓声,紧接着,摇着拨浪鼓的担担匠挑着货担,颤悠颤悠地走进村里,村里孩子跟着他的鼓声快乐地跑过一道道巷子,一条条山坡。担担匠一边走一边摇着拨浪鼓,嘴里哼唱着朗朗上口的招徕声:
“烂绳头、破鞋底、长头发兑换针线唻。来,小杏(孩)要洋糖,婆姨要针线,老太太买个顶针唻。来,破铜烂铁有没有?麻钱钢镚儿有没有?”
担担匠的嗓音并不十分动听,可是如歌的行板,已经唤醒了静谧的村庄,让许多人很动心了。现在回想那“哐啷”、“哐啷”的声响,虽然不能声振五岳,但足以使整个山村巷陌人声鼎沸了。
担担匠长什么模样,穿戴打扮如何,早已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姓张,叫张白虎,沧桑的脸上总挂着一抹和善的微笑。村里的孩子、女人们一窝蜂儿围住了那对油漆斑驳的货箱,在他们看来,那两只货箱俨然包罗万象的百宝箱,是一个缤纷绚烂的天堂。货箱里盛满琳琅满目的货物,有酱醋调料、针头线脑、各色颜料、小孩的玩具、花头绳、发簪……
那年月,乡村物质极度匮乏,大家都很穷,口袋里很少有余钱。起先,大伙儿只是围观,有些妇女看着颜料丝线有些眼馋心热,便走近前打问一下颜料什么价格,丝线什么价格。为了煽动女人们的购买欲望,这个叫张白虎的担担匠便尽情耍开了嘴皮子:“都来瞧一瞧看一看,不买不要钱。且看这里娃娃红,老品红,品绿,品蓝,淡红,淡绿,淡粉,老金黄,水蓝蓝……”,狡黠的担担匠看出了女人们的心思,诱惑逐渐在升级,“买我的颜料最放心!让一勺,送一勺,带一勺,捎捎带带让你带回18勺!”
女人们的心思渐渐活动开了,有的想要给儿子绣一双虎头鞋,有的思量着该给丈夫染黑那条发白的凡立丁裤子,有的要给远方的情郎绣几双漂亮的花鞋垫……那叫卖声此刻就像火种,点燃了蕴藏在女人们心头的热情,女人们终是按耐不住心头的喜欢,所有人纷纷跑回家去了,她们开始翻箱倒柜,寻找烂绳头、破塑料鞋底子,隔年剪掉的长辫子,有些人甚至把家里传家宝也兜出来了,一枚银戒指,一个女儿满月时婆婆给的银项圈,几块被丈夫包了几层布藏在黑窑深处的袁大头,甚至孩子罩衫上缀着的银鱼、银锁也被纷纷扯下来,一股脑儿拿去换来家里需要的货物。
儿时,常常听见母亲唱一首古老的陕北民歌《绣荷包》,小姐思念着远方的情郎,要给他绣一个荷包寄过去:
“打开钢针包,钢针无一苗,打开针线包,丝线无一条,打发上梅香(丫鬟)东街上跑,东街到西街无一个货郎,南街里闪出一个张发财,梅香把手招,货郎走来了,将担子放在碾盘上,货郎叫大嫂,我打开货箱了,要什么货物尽情由你挑!
钢针要六苗,小针要四苗,扎花花针儿捎两苗;品绿(丝线)要六条,品蓝要四条,水蓝蓝线儿捎两条,品红要六条,淡红要四条,芝麻麻扣线线捎呀捎两条。丝线配好了,拿张纸儿包,恐怕俺的热手手摸呀摸脏了。”
这首民歌小调,鲜活地再现了担担匠卖颜料丝线时一个生动的场面,那时的人情世态跃然纸上。这里,担担匠提供的不仅仅是一苗苗纤细的绣花针,或者色彩斑斓艳丽的丝线,同时给小姐带来了精神寄托,她可以在漫漫长夜,将无边无际的思念,用心一针一线绣在荷包上,用一条条丝线将每一滴相思泪串连起来,寄向远方的意中人儿。
小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货箱里的洋糖、柿饼、糖官。那些好吃的东西散发出一股股甜甜的香味,勾引着村子里一个个小馋虫,孩子们煽动着鼻翼,使劲嗅着那股清甜的香味,整个村庄都仿佛弥漫着一股儿一股儿洋槐花的味道。有家底好的,总会对孩子宠一些,买一把洋糖,再称二斤柿饼。这家的孩子好像炫耀似的会立马剥开花花绿绿的糖纸,将洋糖含在嘴里,并且发出了“嘎嘣”、“嘎嘣”清脆的咀嚼声。别的孩子买不起,就尽量怯怯地躲闪着这清脆的咀嚼声,望着担担匠担子的目光里,渐渐存留了些许羡慕和不舍,也有对父母轻微的抱怨。有的小孩,少不了要在娘腿上缠磨一会儿,哭闹一次,娘迟疑着该怎么劝告孩子?家里上顿不接下顿的困窘,已经磨钝了母亲的智慧,她只好抱着孩子哀哀地哭起来。见没有什么成效,孩子也就偃旗息鼓收煞了脾气。时令渐渐逼近腊月,村里买糖官的人家就多了,他们要买糖官回去敬献给灶王爷,以讨得灶王爷的欢心,让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有一次,担担匠竟然慷慨地撕开一个小塑料袋倒出里面彩色的糖豆,给我们围观的孩子每人分发上一粒。然后,他伸出右手把拨浪鼓高高举过头顶,在阴冷的午后快速摇出一串声响。我们含着糖豆,一点点吮吸着,舍不得立刻咽下去,糖豆很快就融化消失了,我们依然意犹未尽附卷着舌头咂摸那股甜甜的味道。担担匠走后,我们有好久都会回味那种味道,盼望担担匠再次光临。担担匠用那些小商品填补了我们生活中一些零碎的小缺憾,也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美好希望
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担担匠又来了,他的货箱愈发物品齐全丰富,除了大小不等的拨浪鼓,扑克,还有手电筒,洋灯,马灯,尼龙袜子等等不少新鲜玩意儿。我的目光最后被货箱里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塑料哨子牵住了。我喜欢它,喜欢听哨音悠扬地响起,更喜欢看担担匠吹响哨子时的模样。为了让哨音像一条绳子那样拴住孩子们购买的欲望,他撮着厚厚的嘴唇,鼓着腮帮子,把脸憋得通红。那个样子,在孩子们眼中真是既滑稽又可爱。
为了能得到一只响亮的哨子,有的孩子便向父母打滚撒泼地哭闹,一个有主意的女孩儿,自顾自向村里奔去,在门脑上找到母亲藏在那里的钥匙,打开家门,将存钱罐里的所有钢镚儿尽数拿来,也不管现场母亲的脸早已变了颜色,因为她已经心满意足地拿着哨子跑进了一片小树林子里,使劲吹着哨子与百鸟同乐。
担担匠其实很辛苦,他们一天通常要挑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走好几十里山路,阳光晴好的日子还好说,一旦遇到刮风下雨寒冷的天气,就寸步难行,当天的收获也会格外惨淡。有一次,担担匠刚来到村里,便开始下起瓢泼大雨,再要摆摊呐喊看来不行了,他只好闪到我家屋檐下避雨。雨点溅到他的裤腿上,那条补了补丁的裤子很快就被打湿了。祖父有一副古道热肠,隔着玻璃看了不忍心,便招呼担担匠到家里来坐。担担匠进门后,连忙掏出一根纸烟恭敬地递给祖父。祖父摆摆手表示不会吸。他便把香烟夹到耳朵上,打开了话匣子。他很健谈,从他与我祖父的谈话中,得知他们家是从曾祖父那一辈移民到陕北来的,曾祖父是挑着一对筐子发家的,祖父和父亲也是担担匠,现在他已经从事这个行当20年了。他摸了摸刮得发青的下巴说,颇为得意地说:“我现在刚过四十,再挑二十年担子没问题。”
过了不久,担担匠再来时,已经不必挑担子了,他推着一辆崭新的手推车来村里兜售更加新鲜稀奇实用的货物。有一位著名老表演艺术家郭颂演唱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新货郎》,就实实在在再现了货郎在这个时期的生活情况:
打起鼓来,敲起锣来哎,
推着小车来送货,
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
穿着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
秋衣秋裤后头垛,又可身来,又暖和。
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呀,
挠痒痒的老头乐,
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
我给她带来汉白玉的烟袋嘴呀,
乌木的杆呀,
还有那澄碧瓦亮的烟袋活来啊呀……
这一次,我母亲刚去城里卖了鸡蛋手头有几个余钱,便慷慨地给我买了一块我十分喜爱的玩具手表。那些日子,我腕上戴着那个假手表,仿佛戴了只玉镯似的,整日喜滋滋的,在睡梦中都会高兴得笑醒来。
后来,村里有了代销店,卖货的房间又大,货物又丰富齐全,售货员叫憨牛,人也厚道老实。我们的注意力渐渐都投注到憨牛身上了。代销店兼收购破铜烂铁,废旧绳头,以及黄蒿芽,桃仁,杏仁,酸枣核等各种药材。家里需要油盐酱醋了,煤油灯没油了,大人就会立即差遣我们小孩子去代销店购买。如果手头一时半刻没有现钱,还可以赊账,签个字下回去一并还上。憨牛为人虽然厚道,但赊账也是要看脸的,村里人他都熟识,谁家大人人品好,谁家大人耍奸溜滑没有信誉,他心里都有一本账,谁家该赊,谁家不该赊,他铁面无私。村里人说憨牛将担担匠的生意抢走了。当然这是大时代的步伐驱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代销店带来的便利远远胜于货郎,担担匠的身影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再后来,人们大都进城了,喜欢逛连锁店,逛大型商场,村代销店也渐渐关张歇业了。
时代的列车总是一如既往地朝前驶去,不会因为我们喜欢什么,或者留恋什么,就停滞不前。货郎这个行当终是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但是担担匠留在乡间小路上的足迹,依然带着那个时代的温度,出现在诗人的诗句中和歌手甜美的歌声里。担担匠的身影曾经活跃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村镇上,不得不说,他们既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物质便利,同时也为那个时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担担匠曾经到来过,从此他与那个村庄有关了,与那个时代有关了,就是那一条条丝线,斑斓了村里女人们爱美的天性,那一声声美妙的哨音,那一粒粒彩色的糖豆,给村子里孩子一段快乐的童年,让每人编织一个旖旎的梦。
我们如今怀念担担匠,除了怀念他们那种不畏艰辛的劳苦精神,他们就像勤劳的蜜蜂,将甜蜜的种子撒播在祖国大地上各个闭塞的村落里。还十分怀念那个时代淳朴的民风,以货易货,需要不计较得失的心态,你情我愿,各取所需,一点喜欢就可以带来幸福和满足感,一个小小的哨子,一条五彩的丝线,足以让人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