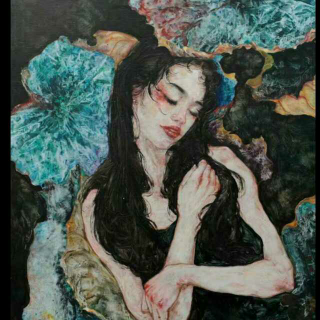
介绍:
母亲的手机
母亲是一个比一般人都需要联系的人。母亲的母亲家离我们家很远很远,远到要坐上两天一夜的火车再加上半天的大巴,才能风尘仆仆的赶到那个充满饭香的小村庄。我随母亲去过那个小村庄,舅舅也从那个小村庄来过我们的家几次。只是无论是舅舅还是我们都是到了目的地,狼吞虎咽的吃过一顿饭,便昏天暗地地睡上一天一夜才能使疲劳的身体适应过来。
所以,母亲极少回去,就只能让书信承载着深深的担忧与思念,翻山越岭地传达到那个遥远的小村庄。
母亲只上过小学,又因为过早地劳动,而把很多文字都忘记了。所以母亲要经常拿着纸笔,托邻居教书的邢老师帮忙写信。母亲一言,邢老师一笔,常常是信纸写了三四张,母亲还在那自顾自地说着。温婉的邢老师便只好把母亲的话,精简的概括起来。即使这样,信件寄走的时候,我们家信件的样子,也总是比别人家的信件饱满许多。
除了写信,母亲也是经常邮寄一些包裹到那个小村庄的。我记得那些包裹中大多是母亲用缝纫机摇出来的衣服,鞋垫,或者是母亲托别人手织的毛衣,毛裤。偶尔会有一些钱。每次母亲寄钱的时候,总会特别在信中的末尾处提到:寄了一些钱过去,不多,注意查收。因为即使是对于一个当时还未上幼儿园的小孩子的我来讲,都懂得,那些钱是多么的来之不易。那是父亲在工地上卖力气的血汗钱;是从一家老小的牙缝里硬生生地省下来的钱。不过即使这样,那些钱中,往往还要凑一些从别人家里借来的钱。因此,每次钱寄出去的时候,母亲总是格外担心,每天都在盼着那小村庄的回信。若如母亲收到回信并听信里说:钱已经收到,家里困难,以后就不要再寄了类似的话,母亲就极其欣喜。你会连续几天的看到母亲唱着歌择菜或忽然间言语多了很多,惹得我们一家都叽叽喳喳,热闹非凡。
小时候的我,会经常看到穿着绿色工作服的邮差来我们家送信。经过几百次甚至上千次的送信过程,每次收到信件的母亲却都像第一次收到信件一样欣喜若狂。久而久之,送信的邮差,每次送到我们家的信件也会格外开心,哥哥,姐姐,我也会跟随着母亲去大门旁迎接那些期盼已久的回信,甚至家里那条养了十几年的老狗-黑子,也会得意的向着邮差摇尾巴。
寄信,收信,俨然已经成了那个时间段我们一大家子最开心的一件事,虽然有时也会有连续几天的担心,但几天的低沉过后又是一个更高程度的极大喜悦。
这种喜悦一直延续到我小学毕业,爸爸的第一部海尔手机打破了这种家庭式的特别的喜悦之感。
爸爸那个时候,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市区上班,星期五下班才骑着电动车从市区赶回家。每个星期五晚上,母亲便拿起爸爸的海尔手机与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小村庄通电话。电话那端传来我们都很难辨识的特别的乡音。然而这陌生的嗓音又来自我们至亲关系的亲人,所以总会有奇怪又亲切的感觉涌上心头。
由于长途电话费太贵。起初我们选择每人说一句话来彼此问候,后来慢慢地改为母亲一个人来与电话那端的声音相互诉说着牵挂与思念。最后,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个小村庄打来或者母亲打去的电话。母亲打电话的时候我们都是随意的甚至是视而不见的。我们看电视,写作业,打哈欠,再也不会因为那个小村庄的消息而无比喜悦起来。唯独只有母亲从未懈怠过,每周五晚上,母亲都会打过去,每次都好像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就强硬地挂断了,但对于母亲来说,每一次都是在做一件无比享受的事情。
直到我都上了高中,班级里每一个同学都有一部按键式的手机,母亲才去镇上的手机营业厅买了她人生第一部完全属于她自己的手机。我记得尤其清楚,那是一部红色带键盘的手机,样子普通到你站在大街上会随时碰到的同款手机。但对于母亲来说,这部手机一点也不普通,她还细心的为这个手机缝制了合适大小的手机套。因为母亲认为,这部手机保存的时间长一点,母亲与那个她魂牵梦绕的小村庄的联系就不会轻易中断。
有了属于自己手机的母亲开始更加频繁的往那个村庄打电话,每次通话的时间仍旧不会长,但电话那端的人由姥姥换成了舅舅又换成了表哥,时间长了,连母亲童年的伙伴都联系上了。这时候的母亲,虽然已经离家22年,却似乎比以往更加了解那个美丽遥远充满饭香的村庄了。
直到前段时间,哥哥把淘汰的智能手机转送给母亲用。很多年不看字,不识字的母亲竟硬生生的逼着自己学会了视频通话。电话那端由抽象的声音变成了熟悉又陌生的的栩栩如生的脸庞。母亲开始啰嗦电话那端的舅舅要少吃,小心高血压。还曾偷偷地对着舅舅发来的新装修好的房子抹眼泪。舅舅的儿媳,孙子也已经和母亲成了无聊时间最亲密的聊天伙伴。
十年如一日,母亲仍然像当年那个未经世事的少妇一样,对每一个有关于那个村庄的消息充满喜悦与期待。母亲的手机让她一直生活在那个承载了她童年与亲人的美丽小村庄里面,即使她与它永隔千山万水。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