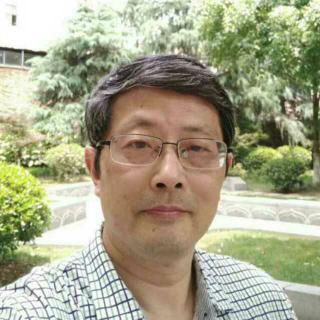
介绍:
古堰秀色永不老
吕云兰
在“有约寻芳苦不晴”的春雨时节,心情多少有些郁闷,单位每月一次的活动,4月11日要去古堰画乡春游踏青。我的心豁然开朗起来,思绪漫进了老家瓯江两岸的秀丽山水中。古堰画乡是由堰头、大港头、保定几个古村落组成的。堰头村位于瓯江北岸,松阴溪畔。保定村、堰头村与我的老家周巷村相邻,以前同属一个公社。每次,我纯正的碧湖乡音就是最妥帖的门票了。
下了公交车,映入眼帘的就是苍劲挺拔,散发出阵阵清香的千年古樟群。春的盎然,欣欣向荣,花团锦簇,清清流水,处处美景,唤起我一种“古堰春色永不老,唤取归来同相处”的感慨。
来到三洞桥边,我伫立桥头,远山近树,风水流韵,深切地感受到千年古堰在心中的份量,油然而生的是一种伟大与骄傲。小时记忆中的古堰堰头村影象,在我脑子里轻轻掠过。第一次走进古代文明,润育碧湖平原万千民众的通济堰,是小学四年级时的远足(以前春游叫远足)。叶洪仁老师给我们介绍三洞桥——水上立交桥的历史,当时只知道三洞桥是这么的神奇,桥上浑水流淌,桥下绿水迢迢。直到今天,古堰成为一方名胜,才知道始创于公元505年的通济堰,比国外最早的拱坝,西班牙人建于16世纪的爱尔其拱坝和意大利人建于1612年的邦达尔多拱坝,要早1000多年。
丽水诗人陶雪亮在《通济堰》中歌颂道:
“像一道横卧的彩虹,
在这里蛰伏了1500年,
说是文物,
却仍是活的,
据说,从这里长出的藤蔓,
绵延整个碧湖平原。”
细细品味这首富于哲理的小诗,心中再次泛起的是一代圣人的丰功伟绩和无量功德。
据史料记载,离拱形大坝500米处,有一条名为‘泉坑’的山坑,其水横贯通济堰渠道,每遇山洪暴发就挟带大量沙砾和卵石冲泄而下,淤塞渠道,使堰水受阻,需经常疏通,影响灌溉效益。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知县王褆按邑人叶秉心的建议,在通济堰上建造了一座立体交叉石函引水桥,俗称‘三洞桥’。把泉坑水从桥面上通过,进入瓯江,渠水从桥下穿流,两者互不相扰,避免了坑水的沙石堵塞堰渠,使渠水畅通无阻,不需年年疏导,真是“石函一成……五十年无工役之扰”也,充分显示了当时设计、建筑的高超水平。1991年,国际友人、日本的福田先生曾站在‘三洞桥’上赞叹说:“当世界上尚无立交桥时,中国人民在这山乡已建造了水上立交桥”。
小学的这次春游,给我的印记最深刻的,还是保定与堰头村之间凤凰山上的石马、石将军雕像,这些雕像雕刻精美,与实际同样大小,石人、石虎、石狗、石马、石羊,对称排列,栩栩如生。现今除两对石马、石将军,已移至万象山公园‘烟雨楼’前外,其他的大多不知所踪。置身于凤凰山上,已无缘再见往日的雕像,作为现代文明人真的要好好的反思了:这难道是古石像的悲哀?丢失的仅仅是石马、石将军吗?真的让人汗颜无地自容。
通济堰也称“官堰”,以前每年,凡是能吃到官堰水的地方,堰头村以下的村庄村民,都要参加修水利,土话叫“做夫”。每年冬天的农闲季节,三洞桥闸门拉下,官堰干涸,各村、各队、各户安排有序,下乡(碧湖以下的村庄,因地势低叫下乡,碧湖以上的地方叫上乡)的农民成群结队,肩扛锄头、畚箕,从堰头村开始,顺堰而下,彻堤坎,刨污泥,通河道。我的外婆家在里河村,每年轮到“做夫”的日子,舅舅顺便就会到我的家里作客。
我们沿着石子路,谈笑风生,约会春天,留下了美景倩影,不知不觉来到通济堰(浙江省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最核心的拱形拦河大坝。我站在瓯江边上,迎着和煦的春风,凝望着眼前的一江春色:江清岸阔,青山隐隐。我想起(宋)晁公溯《通济堰》的诗句:“横江三百丈,遥见石嶙峋”。仿佛觉得岸边绿色的山峦顿时生动了起来,心旌也随之荡漾起来。
拱形大坝初为“木蓧”(即为“筱”,为竹子)构筑,南宋时改为石坝,现存坝保持着拱坝原有古老的结构特色,坝长275米,底宽25米,高2.5米。大坝选址合理,千余年来经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考验,巍然不动。就是由这条拱形拦河大坝拦水到通济堰,自流灌溉碧湖平原,全长22.5公里,分为上中下三源灌区。干渠分凿出支渠48条,支渠再分凿出毛渠321条,并在堰渠上建有大小概闸72座,以调节水量,各渠边又有众多的湖塘储蓄,以备旱时不足,形成以引灌为主,储、泄兼顾的竹枝状水利网。
站在拱形的大坝前,真是感慨万端,走过祖国的多少河山大川,却忽略了恩泽家乡、养育自己的通济堰,写过许多篇游记中,却没有通济堰的片语只言,今天特写下以上文字,作为愧对家乡古代文明的补记。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