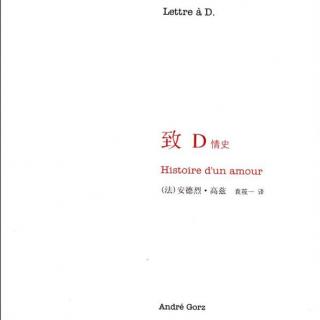
介绍:
P47-61在起名为“你”的一章中,我经常跑题,这一章耗费了很多精力在主题和思考上。《叛徒》在“弗里奥”系列(“弗里奥”是法国伽里玛出版社的一个出版系列)出版后,我不无沮丧地发现了这一点。我几乎没怎么看校样,只是在“你”这一章中加入了我先前删去的九到十页纸,那是我在二十年前为维尔索出版社的英文版所写的内容。这些删节的部分主要是关于罗曼,罗兰的一场论战,其中有足足四页纸是用非常小的字体打成的“详细脚注”。这一关于哲学和革命的跑题也是我故意将“个人冲突简化为冲突模式”的一部分;是我故意“逃离到观念的王国里,在这个王国里,所有的事情都只是某个基本观念的偶然展现”。然而,尽管我揭露出了自己的这种态度,这却并不意味着我就此放弃,不再坚持。这一章接下来的部分所给出的例证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夸张。
这一章应该标志着我生命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应该说明我是多么爱你,不,比这还要美好:是和你一起发现了爱,这份发现终于让我找到了存在的愿望;它还应该说明执子之手的承诺为什么在日后会成为我的存在得以皈依的原动力。故事的陈述却在《叛徒》写完的八年前停下,以我永远不让自己离开你的誓言而告结束。省略号。这一章换了主题,开始描写金钱如何成为人际关系的中心问题,成了对于消费模式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等等,总之,是应该成为下一本书的所有主题。
麻烦在于,在这一章里没有任何关于存在的皈依:没有任何关于我的,或者说我们的爱情发现,没有我们的故事,没有一丁点痕迹。我的誓言只是形式上的。我没有承担起它的重量,也没有将它具体化。相反,我只是以普遍原则的名义对此进行了辩护,仿佛我对此感到羞愧似的。我很清醒,因为我甚至记下了这样一点:“不是吗,我在谈到凯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将她当成处在弱势的小东西来谈的,而且一副抱歉的口吻,仿佛应该为经历这一切感到抱歉似的?”
那么,在这一章里,我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包括在整本书中,我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在谈到你的时候,总带着这么一种漫不经心、高高在上的神气?为什么我给了你那么一点可怜的位置,然而就在这么一点可怜的位置里,你的形象也总是变形的,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为什么即便是影射到我们的爱情故事的片言只语,也总是要和另一个故事交织在一起,另一个我津津乐道于分析的,有关失败爱情和坚决分手的故事?这是我在不无沮丧地重读这部作品时,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显然,我的动机首先是一种几乎接近病态的需要,我需要超越于自己之上,超越自己所经历的,所感觉到的,所想的,固执地将之理论化、知识化,我想成为纯粹的、透明的精神体。
这动机已经贯穿《文集》中。当然,在《叛徒》中它更为显而易见。我希望谈论你的时候,把你当成我一生之中唯一的真爱来谈,而我们的结合对彼此来说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但是很明显,这个故事没能迷住我,这个故事,还有在我写《叛徒》时,在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共同度过的那七年时光。第一次深深地爱上一个人,同时也得到这个人的爱,以前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太平庸,太个人,太普通:这不是能够让我进入普遍意义的物质。相反,失败的、不可能的爱情才是高贵文学的范畴。我一向只在失败和虚无之美中感觉自在,而不是成功和肯定之中。我必须位于你我之上,不惜以损害我们,损害你为代价,借助超越我们个体存在的思考。
这一章的目的正在于揭示这样一种态度,在于揭示正是这样的态度将我们带到了分离和中断的边缘。为了不失去你,我必须选择:要么根据自己抽象的原则,过没有你的日子;要么挣脱这些原则,和你在一起生活:“……比起这些原则,他更喜欢凯;但这是他不太情愿的,无意识的选择”。无意识,是指没有意识到你默许的,现实的一一而非本源的一牺牲。
我在这里当作一种皈依来陈述的故事接下来却被十一行文字腐蚀了,并且完全背离了这个故事。我所描写的自己和一九四八年春天的状态是一样的:不适合生活。“在这个六平方米的天地里,他们度过了共同生活……他一言不发地出出进进,终日埋首于稿纸之间,总是用不耐烦的单音节词打发凯。‘你一个人过就够了’,她总是说。的确,在他的生命中,没有给任何一个个体留下些许的位置……因为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体,他不具有任何重要性,而如果有人将之当作个体来迷恋,他对此也不感兴趣。”往后的整整一页我都用在了我自己所谓的“关于爱情和婚姻的做作的长篇大论”上。
我似乎非常严厉地审视了自己的过去。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故事开始七年半以后一一在一九五五年或一九五六年写成的一页半纸上,有六行关于你的描述,我却把你描述成一个可怜的小女孩,“谁也不认识”,在瑞士生活了六个月之后却“不会讲一个法文单词”?然而我却很清楚你有你的朋友圈子,你挣钱挣得比我多,而且英国还有个忠实的朋友在等你下决心嫁给他。为什么我会写下这些令人厌恶的文字:“如果他放弃她,凯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摧毁……”九页之后,在关于我的“誓言”部分,还有五行毒药。你曾经对我说过一一这是出于我的漫不经心所做出的预见^如果“我们只是在一起度过短暂的时光,(你)情愿现在就离开,这样还能保留关于我们爱情的美好回忆”。我显露出被打击的样子,但是又一次把你描绘成一个小可怜:
“……如果他让凯走,如果他一生都要想着,她不知道将有关他的回忆带到了什么地方,在照顾病人或负起某个家庭的责任中找寻避处。……他就是一个叛徒,一个胆小鬼。而且,如果说他还不确定是否能和她共同生活,他能够确定的是,他不能失去她。他抱紧了凯,带着某种解脱说:‘如果你走,我就跟着你。我不能忍受自己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你走’”,过了一会儿后,他又补充道:“永远不能。”
实际上,当时我说的是:“我爱你。”但是在我的陈述中,这句话却没有出现。
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们的分手对你而言比对我而言要更加不堪承受?就是不愿意承认事实恰恰相反呢?为什么我要说我应该为你的生活“处于目前这样一种形式”而负责,要说“我有责任”让你的生活“更为舒适”?总的算起来,在二十页纸中,出现了三剂,十一行毒药;三次降低你的价值,让你变形的轻描淡写,那是在我们开始共同生活了的七年之后;正是这三剂毒药剥夺了我们七年共同生活的意义。
是谁写了这十一行文字?我想说的是,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我?我必须要重建我们的这七年生活,要讲清楚对于我而言,你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份需求是如此迫切,简直令我疼痛。在这里我已经尝试着建立起我们爱情故事和夫妻关系的整体框架。我却还没有能够充分挖掘我写下这些文字时的那段时间。我应该在那段时间里找寻解释。我记得一九五五年可以算得上是幸福的一年。我换了一家报社。我们一起在大西洋海岸度假。我在第十一区开始了《叛徒》的写作,人处在深深的惶恐中。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签下了学士街的租房合同。我们经历了满怀幸福和希望的时刻。
但是;我越往下写,手稿中的政治成分就越浓。“你”这一章还是顽固地对个人、私人关系进行了定位,包括爱情关系和夫妻关系,当然,我是将其放置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定义的。纪德在他的《日记》中曾经提到过,他总是把前一本书当成后一本书的对立面来看待。我也同样如此。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对于自我的探索几乎是一条死胡同。我们无法再重写一遍。我已经在准备下一本书了,虽然它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义,那时我正在读让-伊夫,卡尔维(1927—2010,法国哲学家、shen学家)的《马克思》,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一些作品以及伊萨克,多伊彻(119D7—1967,英国历史学家、记者,原籍波兰)的《斯大林》。我有点像卡齐米日,布兰迪斯(波兰作家,电影剧作家)在《保卫格林纳达》中所描写的那群剧团成员一样,希望自己勾勒的所有精神运动都能够符合党的要求,并且每个人都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每个人在内心深处对于自己承担的任务都有所保留。我也几乎将爱情看成一种小资的情感。
我“总是用一种抱歉的口吻谈论你,将你当成处在弱势的小东西”(这是我在《叛徒》中所做的说明,现在看来很说明问题卜很显然),我把你表现出来的依恋当作是弱势的表现,至少在我写的东西里是这样的。弗朗索瓦,阿尔瓦勒曾在那时对我说过:“你有一个革命者的痼癖。”你不无焦虑地一一有时是不无愤怒地一一看着我渐渐地转向亲共的一面。与此同时你让我喜欢上我们私人空间和公共生活的扩展。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的一句话很能简要概括我那时的精神状况:“我对你的爱不讨我喜欢。”我不喜欢爱上你的自己。
最终我懂得,我站在法国&``&那一面的理由都很糟糕;不久以后我也明白了,知识分子并不能推动法国&``&的改变。一九五七年初我们新结交的一些朋友让我得到了改变,当然还有新的阅读,尤其是大卫•里斯曼(美国社会学家、律师、教育)和查尔斯•怀特•米尔斯(美国社会学家)的作品。
待到《叛徒》终于出版,我才重新意识到我欠你的是什么:你把你的一切都给了我,帮助我成为现在的我。在给你的一册书上,我题道:
“给你,我的凯,你把你给了我,你把我给了我。”
如果我在这之前能够在“我的书”中充分展开这一点多好。
我必须退后一步,才能够将我们的故事接着讲下去。在我们住在学士街的那几年,我们渐渐摆脱了物质上的困窘。但是我们的消费水准从来都没有跟上我们的购买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俩之间有默契。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我是说,在什么能够赋予生活意义,什么有可能剥夺生活意义的问题上,我们有相同的想法。我记得我一直以来就很讨厌所谓“富裕”的生活方式,讨厌浪费。你也拒绝追随时尚,对时尚你一向有自己的看法。你拒绝为广告和营销所左右,只要你不觉得需要,你就不会买。度假的时候,在西班牙,我们住在“当地居民”家里,在意大利,我们不是住在小饭店就是住在简朴的、包食宿的旅馆里。一九六八年我们才第一次住进一家大饭店,那是在意大利布诺秋索度假村。我们共同生活十年后,终于有了一辆老式的奥斯汀轿车。不过我们还是拥有个人的“机械化装备”,这都是因为那该死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