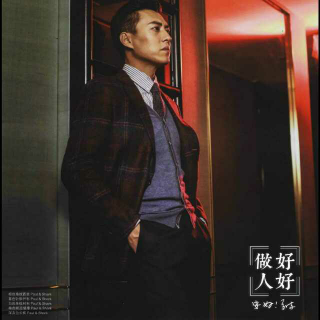
介绍:
明楼大哥问你今天读书了吗 | 靳东
2016-01-27 时装男士杂志
采访/文 吕彦妮
靳东出生在冬至日。
自中国古代始,便有对于冬至节气的分期,「一候蚯蚓结,二候糜角解,候水泉动」。皆意在表述这时天地万物又阴转阳的时节,太阳升起落下的轨道正在慢慢变化,山泉也已经恢复流动,并温热。
靳东以这样的言词在社交网络上解说自己的生辰日,一日以内便获得近三万次的转发量,老派姿态得体妥当,是当下难见的温润。靳东其人亦然。
他的受欢迎程度在刚刚过去的 2015 年呈现出了一种喷发的势态。两部电视剧的热播让人们见到了他细致精准的表演和深沉内敛的魅力。在微博上,以「明楼大哥问你今天读书了吗」的话题轻轻松松冲上百万。他的繁体字表达和对古文的喜好都成为了拥趸们追随的缘由。采访前,在网路上抛出问题「靳东采访指南,请讲」,一时间收到数百条回复,几乎都是善意的提醒:不要聊私事多聊戏剧多聊事业……
谈及自己的事业,靳东言谈滔滔不绝而有理有据。他讲的故事不多,道理却深邃。言毕及理想和现实的沟壑,文化与城池的关联。
「我对现在学生受到的教育,乃至我们共同面对的生活现状,一直是担忧的」。采访时,他特别复述了前日和李健在人民大学的对谈中,自己的主张」。
「怎么才能够被称之为一个文明社会?我觉得是,每个人存在,不管你做任何一个职业,做任何一件事情,起码都应该为整个生存群体,或多或少去做一点什么」。
这是靳东的表达方式,宏大而隆重,令人不自觉仰望。
世界级的戏剧大师铃木忠志曾经在多个场合给过戏剧工作者以忠告,「不要每天只想着戏剧,要和所有的人都这样去传递信息,要为了人类和未来的信念做戏,不然不要做。为了自己的兴趣什么的,我不喜欢这样的说法」。他甚至不喜别人唤他是日本戏剧大师,「我是日本人,这是事实,但是我做的不是日本的戏剧……艺术家应该是超越国家和民族,和整个人类对话的」。
这也是靳东对自己这份职业的认识与理解。
「我想一个戏剧家应该首先是一个文学家、一个哲学家,还要是一个政治学家,甚至一个社会学家,因为戏剧本身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贡献,丝毫不亚于文学、文字、考古、建筑等等一切已经存在、已经矗在那里的东西」。
他想起自己母校—中央戏剧学院的图书馆。「全世界所有中文版戏剧图书里最全的一间」,他很自豪曾经在那个图书馆里面「厮混」了那么久,读了那么多东西。「从那时候终于懂得什么叫‘神交古人’」。
他喜欢萨特,这个法国男人的哲思让靳东着迷。大三时开始「戏剧片段」练习之后,他就总选择他的戏来排。平素阅读大多看过便罢了,做片段练习要求他必须一句一句揣摩台词的涵义,在脑中构想舞台美术的样貌,在空间和字句里找到意义。「它自然而然让我联想到了,萨特当年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的剧本?那个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这个剧本里所呈现的人物,在当时是怎样的存在?」其情类似于一种「考古」状态,从一位剧作家、一个剧本里面,回溯历史,在这些枝枝蔓蔓中找到人类发展长河中的细沙与规律。
所以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他出演的角色总是令人可信,且充满着虚实相交的不确定性魅力。「演员身上应该有历史感,他能够代表人类存在,即使是去去演一个非常遥远的人,也能让人信服」。靳东说。
中央戏剧学院 99 级毕业大戏,乌尔利希·贝希尔的剧作《屠夫》,靳东出演男主角—个年龄在 50 岁上下的屠夫。
那个夏天,《北京晚报》曾经登载过一篇报道,说北京舞台上正同时有两个「屠夫」在唱「对台戏」,「两个最瘦的屠夫」,一个是靳东,另一个是距离几里之外的北京人艺版屠夫,扮演者是教科书一般的老艺术家朱旭。靳东回想起当年,因为自己的演出,错过了观摩朱旭老师表演的机会,但在当时,这是他自主的选择,「我不愿意去看,我不愿意受任何人的影响」。
后来,他演出的版本还受邀代表中国青年戏剧人去参加了国际戏剧节。
他还是喜欢严肃题材的戏剧,因为「它传递的东西也契合我们人类生存的现状,我们的苦难是远远大于快乐的」。
他言谈间眉头渐渐拧紧,有危机感一直如影随形。这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时代,一切东西都要快快快,再快一点。
「我的根源是戏剧出身,我花了四年的时间在不眠不休地学习这项能力。现在看到它正一点一点地依附在了金钱和利益上面……」
靳东想要的,是自己有能力一直爱己所爱,也有能力保护自己一直去爱这样东西的能力。
「今天的人都浮躁,更多的是各扫门前雪,管好自己,一切以只要我能吃饱,我能有更多的物质为中心。但我并不觉得物质能给带来多大快乐」。
他快乐来源是什么?
「35 岁之前,我都慎用‘幸福’这两个字,现在可以提及的快乐和愉悦,除了家庭和家人带来的,更多的就是我的事业,能或多或少的影响一些人的生活态度,这是我最大的快乐」。他希望人们无论做任何一个行业,都坚守「内容为王」的信念。只是他也知道现实所迫,这是理想状态。但是「只有有忧虑,才会付诸于实际行动」。
问他,担忧有的时候会让人变得无力,你有这种无力感吗?
他点头,脱口而出的「有」字重重砸在手心里。「好在我骨子里有与生俱来的一股劲儿。别人越是告诉我这条路行不通了,我却偏偏要(去做),我只是想给我自己一个答复」。
从进戏剧学院到今年已经 16 年,他言辞凿凿地说,「从来到北京考学的那一天算起到今天,我从来没有送过一分钱礼,没有向任何人去摇尾乞怜,只为了得到一个角色。恰恰相反,我宁愿没有作品,宁愿不去演所谓能挣到大钱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我宁愿只是很清贫的坚守在话剧舞台上,也要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从事戏
剧的工作者的态度」。
靳东便是以这样的姿态冲出水面的,应当可被称为「一种理想主义的胜利」。
前阵子,他大学时候的师哥、舞台美术系毕业的韩江又给他发信息,「咱们的剧社又出新作品了!」靳东笑笑地给我看他们的微信对话,一脸自豪又欣慰,说你看啊毕业 10 多年了又商业又艺术的搞过一圈,最后还是回到戏剧上了,还成立了自己的剧社,戏一个接一个的还挺热闹。他喊这些人是自己的「亲人」,也已经不止一次接到来自亲人的召唤。
自不必心急,他回到舞台上,是早晚的事。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