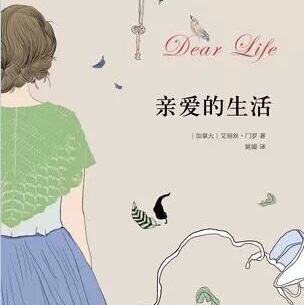
介绍:
在《亲爱的生活》中,门罗的观点太过实际,由此还不能称作乐观。她并不假设事事都会好起来,只是暗示事情会有转机,而且是以大家都料想不到的方式。然而在对生活的叙述中,她总是欣赏那些偶然的转机,几乎可说是对它们钟情了。本书中有一个叫《骄傲》的迷人故事,她的注意力转向了两个凄惨孤独的人。他(她)们正渐渐迈入悲哀寂寞、与人疏远的晚年,生活的小镇已经变得陌生,因此也不再属于他们。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一辈子残疾的兔唇男人。在书中他没有名字,跟母亲住在一起。他不跟任何人交朋友,以免别人同情他。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身不由己地和一个叫奥奈达的女人陷入了一段友谊。
“我一定是在那些年里遇见了奥奈达,之后就和她的生活扯上了关系。“他在1940年代说。
大概是这样吧。她父亲正好在欧洲胜利日的前夕去世,于是葬礼和庆典就在一起尴尬地举办了。来年夏天,就在人人得知原子弹爆炸事件时,我母亲也去世了。她去世得更突然,当时她正在大庭广众之下工作,刚刚说完“我得坐一下。”这事就发生了。
奥奈达是小镇上最知名的人物——银行家的女儿。透过小城里人们知道消息的方式,她对他略有了解,而且相当唐突地——他是一个簿记员,她在街上遇见他——向他咨询卖房子的事。她没什么目标,运气不好,做事心血来潮。而随着时间过去,她越来越被讲述者吸引,他是她的过去当中依然没有变化的那部分。她漫不经心地罔视他的建议,把房子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了一个男人。那人对她说他想在房子里抚养几个孩子,事实上他是把房子拆掉修了一栋公寓。之后就像她盲目地卖掉房子那样,奥奈达搬进了公寓的顶楼。她喜欢那儿的风景,她的风景。
不经意间,奥奈达开始在晚上出现在讲述者的房子里,他们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一起在起居室边吃晚餐边看电视。他生病时,奥奈达就守在那儿照料他好起来。她暗示他她也可以搬进来。对读者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既成的结局,故事就是这么导向的。但是门罗却没有被故事引着走,她是在讲故事。讲述者的个性奇怪,他对此事做出的反应完全让人意想不到:第二天他就把这所自出生以来一直住着的房子卖了。
搬家当天奥奈达来了,跟他有一场谈话,谈的是无关紧要的事,不带什么感情,拉拉杂杂的,有一些沉闷。她想着他们认识彼此已有多长时间了。然后,突然间,她跳了起来——她看见窗外有什么东西,是一只旧的鸟澡盆:
里面满是鸟儿,黑白间杂,在里面扑腾。
不是鸟儿。
是比知更鸟大,比乌鸦小的东西。
是臭鼬。小臭鼬。俩人肩并肩站着,都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失意的生活:
可是多美啊。闪耀着,舞蹈着……
我们观看的时候,它们一个接一个从水里爬出来,接着穿过了院子,动作很快,然而走的是一条直直的对角线。就好似它们很为自己骄傲,同时又很谨慎。它们有五只。
“天哪,”奥奈达说,“在城里。”
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讲述者和奥奈达的局限——他生活的一成不变,奥奈达生活的漫无目的——所有这些都得以呈现出某种尊严,就像那五只美丽的臭鼬在水里闪闪发光。在世作家中没有别人能这样揭露生活的乏味了,然而门罗的作品如此令人心碎的原因是:无论人物多有缺陷,我们也无法蔑视他(她)们;无论风景有多荒凉,我们也无法把眼睛转开。“可是多美啊!”一个倒霉的,被宠坏的老姑娘;一个困窘的、残疾的隐士,还有阳光下的五只小臭鼬。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