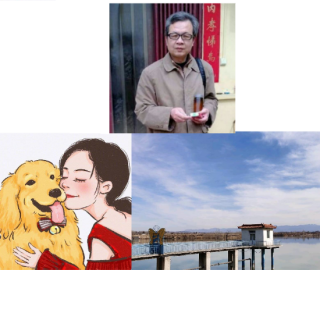
介绍:
我长久的种豆体验非常独特,播种、锄草、收获、脱粒、挑选、卖掉----这最后一桩事最难——我或许得加上吃,因为我还真品尝了。我是下决心了解豆子。当他们正在生长的时候,我常常是从早上五点钟开始一直锄到正午,通常一天剩下的时间做别的事情。想想那些一个人和各种各样野草的亲密和好奇的交往——的确需要稍微说说,因为关于它在劳作描述里还少有提及——如此无情地扰乱它们那精妙的组织,用他的锄头做如此引来怨恨的区别,削平一个种类的所有阶层,孜孜不倦地耕作另一个属群。那是罗马苦艾——那是藜芦——那是酸模——那是风笛草——瞄准他,翻起他,刨他的根翻晒在太阳下,别让他和阴凉处根断丝连,要是真那样他会把自己转向另一边露头,两天的工夫就又绿得如同韭菜。一场持久战,不是与鹤,而是和野草;那些特洛伊人,太阳、雨和露水在他们一边。每天豆子们看到我武装起一把锄头来救他们了,去削掉他们敌人的脑袋,在战壕布满野草的尸体。好多精力健旺高高在上——招摇的赫克托,高出他拥挤的同伴足有一呎,在我的武器前倒下,滚进了尘埃。
那些夏天的日子我的一些同代人们投身于波士顿或罗马精美的艺术,另一些人们去印度冥想,还有些人去纽约或伦敦做买卖。我就这样,和新英格兰的农夫一起,投身于农事。并不是我想要豆子吃,因为我天生是一个毕达哥拉斯信徒,至于豆子,它们迄今为止是否就意味着煮粥或投票,还有用来交换大米;抑或,偶尔地,由于某些人必须在田地里工作哪怕仅仅是为了转义和表达的需要,有一天去服务于一个寓言制造者。从整体上它曾是一种难得的娱乐,已经延续好久了,现在也许已经被消解。虽然我没有给豆子施肥,也没有一次性把他们锄遍,我通常锄得并不坏,在我脚步所及,而且最后也为此得到回报,“这是真理,”就像伊芙林所说,“没有任何堆粪或其它化肥可以与这种持续运动、强力犒劳和用铁锹翻土相比。” “土壤,”他在别的地方补充,“特别是新的,有某种磁力,通过它可以吸引盐、能量或美德(也这样称呼)赋予其生命,而且我们对土地所有的劳作和搅动在滋养我们自身,这是合乎逻辑的;而所有的大粪和其他污物都只不过是这种推进的替代品。”更甚者,这是 “废弃和地力耗尽、正享受自己安息日的”土地之一,已经是碰巧如同肯纳尔姆•迪格比爵士认为的那样,从空气中吸收了“活力的精灵”。我收获了十二蒲式耳的豆子。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