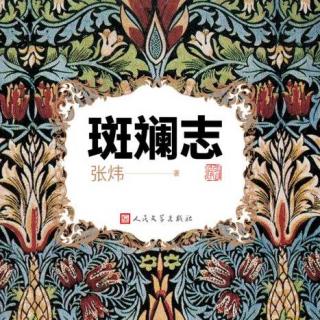
介绍:
检索诗人自己以及有关的庞大文字,会发现斑驳陆离颜色缤纷,应有尽有。如果将其一生划分为尽责和享受这两个部分,可以说都得到了详尽的记录。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最容易被他人罗列功业,像如何解决民生问题、诸多政绩等,都不会遗漏。不过这一切仍旧无法掩盖和排除另一面:他作为一个大权在握者的任性,还有奢侈。我们后人津津乐道于诗人修造的密州超然台、杭州的迎宾官船,还有其他一些莺歌燕舞之盛;在徐州修筑起十丈高的黄楼,是宴请海内风流雅士之地,欢歌通宵达旦。这一切也只有身居高位的人才可以兴办。虽然这在当年远非个别奢华 ,但也是可为可不为之事,所以只能视之为一种放任和享受。那些脍炙人口的娱乐场所的描述,既记录了他的作为,也载下了他的“潇洒”。
他初达密州时曾有讶异,因为与之前经历的杭州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他在《蝶恋花·密州上元》中写道:“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这个时期正好是新法推行之时,以往配给的大量公务接待费骤减,这让喜欢大宴宾朋的苏东坡非常郁闷。他对新法更加憎恶:不仅危害黎民,而且还殃及自身。其实自古以来官场的奢华都为人痛恨,因为实际情形往往是黎民不得果腹,官人却大腹便便。花钱如流水,没有节制,那种遏制权力的力量当然很难来自权力本身。王安石作为一个改革者,以及所有类似的改革者,其动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于自身的拒绝。这其实是最困难的一个动作。在这方面,即便是理性和仁善的苏东坡也不免有些惶惑。密州期间,因为没有钱财挥霍而发出的抱怨就记在诗中,而且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少有愧疚。过惯了阔绰日子的苏东坡,是极不习惯于这种清贫生活的,物质上的挥洒自如与纸上的浪漫豪情大多是一致的。他在这两个时刻都同样慷慨,同样放肆,这既是他的局限,又是当权者的局限、人性的局限。他的超越和仁慈,只在另一些具体的场合流露出来,就像他不能时时豪气大发、诗才迸溅一样。
走出眉山之后,他如愿以偿登上高位,加入了另一个阶层。后来厄运降临,他不得不一次次成为罪人。但这时他已经享有盛名,作为一个贬谪之人,仍然能够享受到其他人难以拥有的东西。盛名之下,一切自然不同。虽然已为罪身,每到一地还是有地方官员送酒送肉,即便是负责看管他的最高首长也对其另眼相看,关爱有加。在谪居黄州的时期,太守徐君猷居然成为他的好友:“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此意岂可忘哉!”(《与徐得之》)这封信是写给徐得之的,他是徐君猷的弟弟,也是诗人的好友。这个徐太守后来调赴湖南途中不幸病逝。东坡以戴罪之身居于黄州,徐太守还经常带上自己三个年轻漂亮的侍妾和上好的酒菜,邀诗人登上栖霞楼宴饮,不醉不归。也许这时的苏东坡不敢把自己当成一个高高在上的特殊人物,可是其他人、包括后来人,却一定让他做这样的人物。
平心而论,好的官吏不是不能享受,而是享用“应得”的一份,不能掠取和贪婪。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就这个标准来说,苏东坡算是一个“合格”的官吏。他对于美食、豪居、朋友、女子,皆能受用、体贴、爱护和体味,在这些方面既有很高的要求,又能随遇而安,择其长处而用之。作为一位仕人,他应对裕如,不曾懈怠,每到一地都有美谈,所谓“官声甚好”。我们以前谈过他在登州任职仅仅五天,加上逗留盘桓也不超过半月,却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工作效率之高无人能出其右。更惊人的是他在京城担任断案职务时表现出的异能:本来政敌想用无比繁琐的案件牵扯其精力,使他无暇言政,却想不到他竟然干得那么出色。记载中他处理公文总是一挥而就,却又毫无疏失,实在是为政的天才。就享受与尽责这两个方面看,他似乎都做到了极致。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