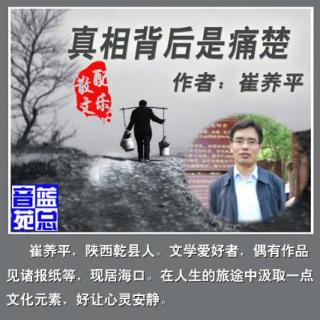
介绍:
崔养平,陕西乾县人,文学爱好者,偶有作品见诸报纸等,现居海口。在人生的旅途中汲取一点文化元素,好让心灵安静。
《真相背后是痛楚》
文Ⅱ舟羿(海南海口)
题记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诞辰74周年。 一一您的儿子
我的家乡人把撒谎叫“糟怪”。这是一句乾州俚语,是农村人对说虚话哄人、用假话唬弄人行为的口头禅。糟怪不算做骂人的话,本身并没多少恶意,无非是语气上有一点埋怨弹嫌的意思。
1
我上初中那三年,家里连续发生了几件大的事情,每件花销都很惊人。先是建房子,家里人口多,原来的两孔窑洞早就不够住了,父母亲利用多年来的积蓄,又欠了些帐,在亲戚们帮忙下起了四间半厦子房。跟着没多久,哥哥不幸得了一场大病,差点丢掉了性命,父母曰夜奔走,又摊了一堆债务,总算是把人救了回来。一年后在亲戚介绍下,休学的哥哥离家当了工厂学徒工,押金1500元全是借的。那几年正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农民们才刚刚解决了吃饭问题,家家都穷得叮当响,一分钱都恨不得掰开来使。经过接连几次大的折腾,我们家穷得跟水冲洗过一样,那几年里,卖粮还帐成了父母的主要话题。我深深记得有一年大忙天,家里没油了,也没钱买,父母亲就水煮青菜面条,寡汤淡水,硬撑着身体从繁重的劳动中熬煎下来。短短几年,正当壮年的父母亲一下子憔悴了许多:母亲本来干瘦,人显得更矮了;魁梧的父亲背开始有点驼了,白发占据了两鬓,皱纹堆满了额头。巨大的债务压力使得俩人大多时候愁容满面,很难看到笑脸。
家里经济拮据,学生娃也不会闲着。每个暑假,我和弟弟除了割草喂牛干家务,承担些力所能及的庄稼活,还会干一些副业营生,譬如白天到山沟里挖药材,晚上去坡道上逮蝎子,这样一个假期还能帮家里补贴点零花钱。当中最主要的一项收入是卖槐米,我家有四棵高大苍老的土槐树,能出产二三十斤左右的槐米,每年靠它基本上填补了我和弟弟学杂费的缺。1987年夏天,离开学没几天了,村口都没来收购槐米的中药贩子,无奈之下父亲决定把槐米送到西安的中药铺换钱。吃罢晌午饭,揣上母亲包好的两片锅盔馍,父亲用自行车推着槐米,带着我赶往镇上,搭乘从马里上来的长途汽车。
到了镇上,车还没来。父亲蹲在路边,忙着用纸条给自己多卷几根旱烟卷。这时候我央求道:“大,我也想到西安看看,带上我吧!”从小到大,我还没迈出过农村,对城市的印象也只是从在西安上学的二姐嘴里听听而己,趁着这个机会能去见识一下该多好。“大,我跟你一起去吧,你看,我还能帮你扛槐米呢!”我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并不强壮的胳膊。
父亲面有难色,手却丝毫不停。未了,头也不抬地说:“这回你就不去了,我一个人扛得动。再说,你跟去了,你妈一个人照看屋里,牛咋办?”最终父亲一个人去了西安,我极不情愿地骑车回了家。
第二天晌午时分,父亲回来了。母亲赶紧端出饭来,父亲一气吃了三大老碗。旁边的母亲心疼地问出门咋吃的饭,父亲抹了抹嘴,满意地抻抻腰,边点烟边高兴地说:“你再甭操心咧,昨个晚上杜宏春给我下了一大老碗硬扯面,把我咥得个美!”说着,从烟盒里掏出一卷钱交给母亲,“这回槐籽卖得好,多亏杜宏春今早带我去找了个熟人,一斤多卖了一块多,把路费包住还能长一些。人家杜宏春啥也没要还把我送到玉祥门车站,真麻烦得很!”又别过头对我说:“你好好念书,将来跟你二姐一样,有的是去西安的时候。”我不愿听,负气走开了。没有去得成西安,少年的心多少有些遗憾,这件事也就记了下来。
很多年后和母亲聊天,方知父亲不带我的原因:还是没钱。父亲去时的车费都欠着,卖了槐米,回程时才一并付清。
2
1995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宝鸡市桥南一家有6000余名职工的大型国企工厂工作,这也是我真正地开始融入和了解城市人的生活。快到年底了,有一天晚上加班,很晚才回居住的单身职工楼。一个人走在空寂的马路上,冷飕飕的夹道凛风吹得人脸皮生疼,无心他顾,我缩着脖子埋头快走。
“碎爷”,传来一声苍老的胆怯的声音。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寻声搜索,铁栅栏门口昏黄路灯下有一个瘦削的身影。看到我驻足,那人赶紧小跑几步,来到我跟前,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碎爷,我打听个人!”男人急切的说。
我不好意思起来,“叔,啥事?您不要这样喊我了,我还年轻。”
“我寻个我村人,叫王根盛。你知道不?”
“叔,我不知道。我来这厂子才几个月,认人不多。”我认真地拒绝了。
男人浑浊的眼睛一下子黯淡起来,喃喃自语:“哦,就是的。”
我抬脚准备走。突然,多年前父亲到西安卖槐米找杜叔的模拟场景电一样闪过我的脑海。我停了下来,问:“叔,您哪儿人?您找的人多大年纪了?”
男人见有了希望,急着说,“我是千阳的,王根盛是我村子的,比我大两岁,是我三哥。”
“你知道他是哪个部门的?我们厂有6000多人呢。”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