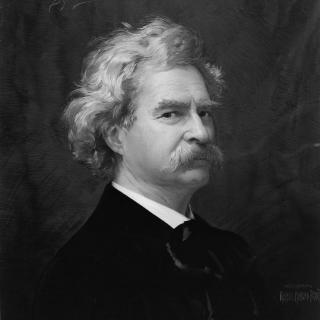
介绍: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圣路易。西进途中,在印第安那州特尔霍特换了车,就有一个四五十岁上下、面目亲善的绅士从小站上来,坐到我身边。同他心情愉快、海阔天空地聊了约一个钟头,我便发现他极有见识,讨人喜欢。他一经得知我从华盛顿来,立即询问起形形色色的政府官员和国会事务来。不久我已明白,与我谈话的是位对首都政治生活了如指掌的人,他甚至连这个国家立法机关里议员们的作事风度和程序仪式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过了一会儿,就见两个男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留了片刻,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哈里斯,要是你肯替我办这件事,我永远忘不了你,老弟。”
我这位新旅伴的眼睛里突然闪出欣喜的亮光。好像那人的话勾起了他一段快乐的回忆。顷刻,他又露出一副思虑重重的面孔——简直有些闷闷不乐了。他转头对我说,“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让我把我生活中的一段秘事告诉你。这段秘事自发生后,我从来都不曾提起过。请耐心地听,答应我别打断我的话。”
我说没问题,他就如此这般地讲了下面的一段奇遇。讲解过程中时而情感迸发,时而阴郁低沉,但总是极其认真诚恳。
那是1853年12月19日,我从圣路易乘夜班火车去芝加哥。车上总共只有24名乘客。没有妇女,也没有小孩。我们的兴致很好,大家很快就混熟了。看来,这是一次快乐舒心的旅行;我猜这一伙人中压根儿就没有一位预感到很快就要经历的那种恐怖局面。
晚上十一点钟,天下起大雪来。火车刚一离开那个名叫韦尔登的小村,就进入空旷寂寥的大草原。千里荒原,渺无人烟,一直延展到朱必利定居点。狂风呼啸着刮过平展展的荒地。那儿没有树木,没有山丘,甚至连七零八落的岩石也见不到,所以风刮起来毫无阻挡。随风飞扬的雪花,就像狂风暴雨在海浪尖上激起的浪花。雪越积越深,车速减慢。我们知道,这是火车头在积雪中开路越来越费劲了。说实在的,有时候它简直就停止不动了。大风在轨道上堆积起一个个大雪堆,活像一座座坟山。聊天也没有劲儿了。欢乐让位给焦虑。要是被大雪困住,待在荒凉的大草原上,方圆50英里可都没有人家——这种想法浮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把大家都弄得精神非常颓丧。
凌晨两点,四周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我从不得安宁的睡眠中惊醒。可怕的实情顿时闪过我的心头——我们成了雪堆里的囚徒!“全体起来动手自救!”大家一跃而起去执行这道命令。夜茫茫漆黑一片。铺天盖地的大雪,势不可挡的风暴,大家从车厢跳进这样一个世界,心里都明白,现在要争分夺秒,要不就会有灭顶之灾。铲子、手、木板——凡是能清除积雪的东西立刻都用上了。那真是一副离奇的景象:一小撮发狂似的人跟越堆越高的积雪拼搏。雪堆下半截隐没在黑黢黢的阴影里,上半截暴露在车头反光灯炽烈的灯光下。
短短的一个小时就足以证明我们在白费力气。暴风雪积成了十几个雪堆,把路轨阻塞了,而我们仅仅刨掉了一个。更加糟糕的是,人们发现,刚才火车头对敌人发起冲锋时已经把主动轮的纵向轴弄断了!即使铁路畅通无阻,我们也无可奈何了。我们干活儿干得精疲力竭,心里又不是滋味,便进了车厢。大家围着火炉严肃地讨论眼下的处境。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大伙儿最窝心的就是这一点。我们是不会冻死的,因为煤水车里有的是木头,这是我们惟一的安慰。讨论到最后,大家都接受了列车员令人丧气的结论,就是说,谁想徒步在这样的雪地里走50英里路,那就等于去寻死。我们无法派人去求援,即便我们有办法去,也没人愿意来援助。我们只好听天由命,耐心等待,要么有人来救援,要么就等着饿死!我想,就是最刚强的人一听了这话,心也会马上变凉的。
过了一会儿,谈话变成了一种三三两两的窃窃私语,话题仍离不开火车,这种低语随着阵阵狂风的起落而忽高忽低;灯光昏暗起来;大多数遭难者在忽明忽暗的黑影中安下心来想——忘掉眼前,如果可能的话,——睡觉,如果可以的话。
漫漫无期的长夜——我们觉得的确是漫漫无期的——终于把磨磨蹭蹭的时光打发走了,东方破晓,现出灰冷的晨光,亮光逐渐增强,旅客一个接一个活动起来了,显示出生命的种种迹象;一个接一个地把耷拉下来的帽子从额头上掀起来,舒展舒展僵硬的四肢,然后从窗户里向外窥视那副萧瑟的景象。的确萧瑟透顶了!——个生物的影子都没有,一个人家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白茫茫的荒野,卷起的雪片随风到处飘扬——一个雪片飞舞的世界遮没了上面的天宇。
我们在车厢周围逛走了整整一天,说得很少,想得挺多。又是一个滞留不去的愁闷的夜晚——还有饥饿。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