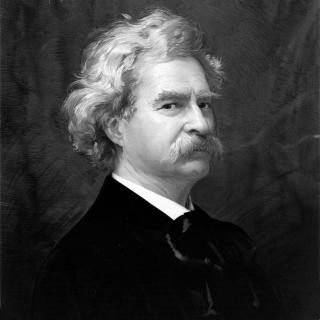
介绍:
我租了百老汇大街尽北头的一间大屋子,在我搬进去之前,那幢古老大厦的上面几层已多年没人住了。那地方早已湮没在灰尘与蛛网中,湮没在一片荒凉与静寂中。头一天晚上,我爬上楼到我的宿舍时,像是在坟墓间摸索,像是在侵入一片死者的禁区。有生以来第一次,一种迷信的恐惧控制了我;我在楼梯的黑暗中拐了个弯儿,一缕看不见的蛛网的粘丝飘到我脸上,并紧粘在上面,我打了个冷战,好像撞上了幽灵。
我到了我那间屋子里,一下子将霉垢和黑暗都关闭在外面,这才感到相当快慰。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欢,我冲着火坐下,觉得轻松舒畅了。我在那里坐了两个小时,重温往事;我回想起当年的一些情景,竭力使那些已经半遗忘的面庞从迷茫的往昔岁月中重新浮现;我在幻想中留心听那些早已沉寂了的语声,留心听那些一度熟悉,但如今已再无人去唱的歌曲。当我的幻想变得越来越暗淡,那情调变得越来越忧伤时,外面风的呼号也逐渐低沉,好像是一片凄厉的哭声,那猛烈打在窗上的雨减弱了,听来是均匀的啪嗒声,街上的各种声音变得更低沉了,到后来,最末一个晚归的行人的脚步声也在远处消失了,此后再没有声息了。
炉火已快烧尽。我逐渐有一种孤寂冷落感。我站起身,脱了衣服,踮着脚在屋子里来回走,悄悄地做我要做的事,好像四周都是已经入睡的敌人,只要一惊醒他们,我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我盖好了被,躺在床上听风雨声,以及远处百叶窗的吱嘎声,直到这些声音催我进入梦乡。
我睡得很熟,至于睡了多久我却不知道。突然,我醒了过来,浑身颤抖,担心会发生什么事。一切静寂。一切,除了我自己的那颗心——我能听见它在搏跳。过了不一会儿,毯子开始慢慢地向床脚那头滑过去,仿佛什么人在扯它!我不能动弹了;我不能开口了。毯子仍旧满不在意地溜开,直到我的胸部袒露在外面。于是,我奋不顾身,一把揪住了毯子,拉过来蒙住我的头。我等待,我留心听,我等待。是谁又一次开始那样毫不放松地扯,我又一次半死不活地躺在那里,不知过了多久,一秒钟一秒钟地挨过,直到我的胸部又敞露在外面。最后,我鼓起勇气,把毯子拉回到原先的地方,使大劲紧揪住它不放。我等待。又过了一会儿,觉出毯子被轻轻地扯了一下,我又使劲揪住它。它被扯得更加有力,最后是毫不放松地硬扯——而且越扯越有劲。我手松开了,第三次毯子又溜开了。我哼哼了一声。是谁从床脚头应了一声!我脑门子上冒出大颗汗珠。我被吓得魂不附体。立刻,我听见我屋子里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我觉得那好似一头大象的脚步声——它完全不像是人的脚步声。但是它正在从我跟前离开——这使我的紧张有所缓解。我听见它移向房门——穿过门口出去,并没拔插销或开门锁——然后在阴森的过道里游荡开,一路沉重地压着地板和托梁,于是它们又咕喳咕喳地响——然后,又恢复静寂。
一阵紧张激动平息后,我对自己说:“是一场梦——只是一场噩梦。”于是我躺在那里思考这一件事,最后自己相信,这的确是一场梦,这时随着宽慰的笑,我紧闭着的唇松开了,我又感到快慰了。我爬下了床,点亮了灯;我发现门锁和插销跟我刚才关门时一样纹丝未动,这时又一阵宽慰的笑从我心坎中涌起,在我唇边泛开。我取过我的烟斗,点燃了它,刚在炉火前坐下,这时候——烟斗从我麻木的手指间落下,我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平静的呼吸突然被一声喘息打破!就在壁炉前砖地上的炉灰里,和我的赤脚印迹并排,是另一个脚印,那样硕大无朋,我的脚印和它相比之下好像是婴儿的!这样看来,我这里是来过一位不速之客,而这就说明了那大象的脚步声。
我熄了灯,回到床上,吓得瘫软了。我躺了很长时间,偷偷地向黑暗中窥探,一面留心去听。接着我听见头顶上空传来刺耳的声音,好像是谁将一个沉重的东西在地上拖过去;接着那东西被推倒了,随着那一下强烈的震撼,我的窗户发出颤动的回响。我听见大厦中远处一些地方隐隐传来砰砰的关门声。每隔一会儿我就听见偷偷摸摸走着的脚步,是谁在那些过道中掩出掩进,沿楼梯爬上爬下。有时候,这些发出声响的东西移近我的房门,犹豫了一下,又离开了。我听见远处走廊里轻轻地传来锁链的郎当声,留心听着那郎当声越来越近——那是拖着锁链的鬼怪在向前走,疲乏无力地登上楼梯,每登上一级楼梯,那锁链过于长的部分搭拉下来,就响起刺耳的碰撞声。我听见嘟哝不清的人语声;我听见断断续续的,好似被强行压下去的厉号声;我听见肉眼无法看见的衣服传来的窸窣声,肉眼无法看见的翅膀发出的猛烈扇扑声。这时我意识到,我的屋子已被谁侵入——我不是单独一个人。我听见我的床近旁有叹息声,呼吸声,以及神秘的悄语声。就在头顶上空天花板上,现出了三个磷光不太耀眼的小球,有一会工夫它们在那里紧凑在一起闪着光,然后向下坠落——两只落在我脸上,一只落在枕头上。它们像液体般迸溅开,我觉得它们暖洋洋的。我的直觉告诉我,就在下坠的时候,它们已变成一滴滴血水——我无需借灯光证实这一点。接着我就看见一些惨白的面孔,模糊地闪着磷光,再有一些脖子上没脑袋的,就那样高举起苍白的手,在空中浮荡——浮荡了一会儿,接着就消失了。悄语结束,其他声响也停息,然后是一片肃静。我一面等待,一面留心听。我觉得,我必须有灯光,否则我非死不可。我吓得身体都软了。我慢慢地往起坐,这时我的脸碰上了一只冷冰冰、湿腻腻的手!显然我全身所余的气力都消失了,我像受到打击的病残人向后倒去。接着我就听见衣服的簌簌响声——猜想它是冲门口那面穿过屋子,然后走了出去。
当一切又恢复寂静时,我爬下了床,病病歪歪的,用一只手去点煤气灯,手哆嗦得像我一下子老了一百年。灯光给我的精神上带来些微欢欣。我坐下来,迷迷糊糊地沉思,仔细琢磨那炉灰上的巨大脚印。不一会儿,脚印的轮廓开始闪动,变得模糊。我仰起头来望了一眼,原来很宽阔的煤气火焰正在慢慢地缩小。就在那时刻,我又听见那大象般的脚步声。我觉出它是向这里走过来,沿着那散发出霉湿气味的前厅,越走越近,而那灯光也越来越昏暗。脚步一直走到我的房门口,然后停下了——灯光已经昏暗成惨淡的青灰,于是我四周的一切都沉浸在阴森、微弱的光影中。房门并没开,但是我觉出一阵微风吹在我脸上,我立即意识到我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模糊的鬼怪身影。我用中了魔的眼睛注视着它。一片灰白的光在那东西上面悄悄移过;逐渐地,那东西的模糊轮廓显露出形状——现出一只胳膊,然后是两条腿,然后是一个躯干,最后是一张巨大而悲哀的脸,从迷雾中向外望。它那层薄纱的掩蔽物被剥光了,身体裸露了,肌肉遒健,体态端正,那位威风凛凛的卡迪夫巨人呈现在我上方!
我的忧惧全部消失——因为,哪怕是小孩子也会知道,有着那样慈祥面容的人,是不可能给你带来伤害的。我立刻又心花怒放,而那煤气灯也与此相呼应,它的火焰也跟着腾起。从未有过一个孤苦伶仃的人,那样高兴地欢迎他的友伴,像我招呼这位表示友好的巨人。我说:
“怎么,难道那就是你不成?你可知道,刚才两三个小时里,我可被你吓坏了?我真高兴见到你。要是有一把合适的椅子就好了——这儿来,这儿来,千万别去坐那个玩意儿!”
但是我关照得太晚了,我还没来得及阻止,他已经坐下去——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一把椅子被那样压得粉碎。
“别坐,别坐,你会毁了所有……”
这一次又太晚了。又是哗啦一声响,又一把椅子被分解为它原来的组成部分。
“真该死,难道你一点儿自知之明都没有吗?你是要毁了这儿所有的家具吗?过来,过来,你这个石化笨蛋……”
但这也是徒费唇舌。我还没来得及拦住,他已经坐上了床,那是一次伤心触目的破坏。
“喂,这样取闹,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先是跑到这儿来,四下里磕磕撞撞走来走去,还带来了一大伙孤鬼游魂,我可被你们搅得烦死了,后来,我并不介意那些很不雅观的衣着,那是任何其他地方有教养的人士都不能容忍的,除了在一些大戏院里,可即使是在那里,如果属于你这样的性别,赤身裸体,也是不允许的,可是你报答我的方式却是破坏所有你能找到可以坐上去的家具。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给我和你自己带来了同等的损害。你跌坏了你的尾脊骨,在地上洒满了你屁股上落下的碎片,把这地方糟蹋得像一个大理石采石场。你该为自己害臊——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儿,你该更懂事了。”
“好吧,我不再压坏任何家具了。可是,那我怎么办呢?我已经一个世纪没机会坐下了。”说到这里,他眼泪汪汪的。
“可怜的人,”我说,“我不该这样苛责你。再说,你肯定又是一个孤鬼。那么就在这儿地板上坐吧——没其他东西承受得了你的重量——再说,咱们也不能这样相互交朋友,让你高高地凌驾在我上首;我要你降低你的位置,我可以坐在这张账房里用的高凳子上,和你面对面闲聊。”
于是他坐在地板上,点燃了我递给他的烟斗,把我的一条大红毯披在肩上,把我的坐浴浴盆像头盔那样戴在头上,显得既别致又舒坦。接着,趁我去把炉火重新烧旺时,他盘腿坐好,在舒适温暖中展露出他那双硕大无朋的脚,以及平坦的、蜂窠般的脚底。
“你的脚底和腿肚子上是怎么一回事,瞧它们被凿得那样坑坑洼洼的?”
“那是在地狱里生的冻疮——我的冻疮一直溃烂到后脑勺,当时我睡在纽厄尔农场的地底下。但是,我爱那地方;我爱它,就像一个人爱他的老家。没任何其他地方,像我在那儿感到安宁。”
我们闲聊了半个小时,后来我注意到他好像疲倦了,就提醒他。
“倦了吗?”他说,“可不是,我也是这样想。那么现在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因为你待我这样好。我就是对街博物馆里那个石化人的鬼魂。我是巨人卡迪夫的鬼魂。只要人们一天不把那可怜的躯壳重新埋葬好,我就一天得不到安宁。那么,要使人们实现我这愿望,我必然要做的又是什么呢?是吓得他们去采取这一步骤!——是到安放那躯壳的地方作祟!于是我天天夜里都去那博物馆里作祟。我甚至集合了其他的鬼魂去协助我。可是这没用,因为从来没人半夜里去博物馆。于是我想到了这个主意,跑到这儿来小闹一场。我以为,只要是有人肯听我申诉,我一定会达到目的,因为我有的是地狱里最能为我效劳的伙伴。一夜又一夜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