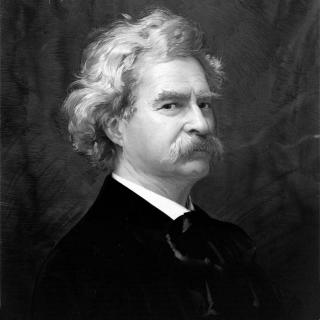
介绍:
我们在百慕大待了四天——有三个晴天,大伙一起外出;一个雨天,都待在屋子里,因为没能租到游艇出航而感到很失望;现在我们的假期已结束,于是大伙又登上了船,一同返回家乡。
乘客中有一个身体极其瘦长、神情显出愁郁的病人,他那憔悴的面容、忍受痛苦的眼光和郁郁寡欢的神态,引起了所有人的同情,也激发了所有人的怜悯。每当他说话时——他是难得开口的——平时他很文静,而这就使所有的听众都对他产生了好感。起航后第二天晚上——当时我们都在吸烟室里——他逐渐加入了众人的谈话。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不知怎的,他谈起了他本人的经历,最后谈了以下这则离奇的故事。
看上去我像是一个六十岁的已婚的人,其实,这是由于我在某种情况下遭受的苦难所造成的,因为我并没结过婚,而且只有四十一岁。你们很难相信,像我这样瘦得像个鬼似的,短短两年前却是一个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人——一个铁打的汉子,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哪!——这说的只是简单的事实。但比这更离奇的却是:我是如何把身体拖垮了的。我之所以变得这样虚弱,是因为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坐火车赶二百英里路,去护送一箱枪支。这可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现在就让我说给你们听听吧。
我家住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两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天刚黑,我在狂风大雪中回到家;一走进门,我首先听到的是我最要好的童年友伴和同学约翰·B.哈克特前一天死了。他的最后遗嘱,是要我把他的遗骸送回到威斯康星州他可怜的年迈双亲那里。我十分震惊和悲痛,但再没时间去哀悼了;我必须立刻上路。我带着那张上面注明有“威斯康星州伯利恒市利瓦伊·哈克特执事”字样的卡片,在风暴呼啸中匆忙赶往火车站。到了那里,我找到了人家向我描绘的那口白松木长棺材;我用几只图钉把卡片钉在棺材上,眼看着它被安全地搬上了快车,然后跑进一家饮食店,吃了一些三明治,并吸了烟。不一会儿,我回到站台上,我托运的那口棺材好像又被人搬下来了,一个年轻人正在旁边仔细地看它,手里拿着一张卡片、几只图钉和一把榔头!我吃了一惊,对这困惑不解。趁他开始钉卡片,我就奔向那列快车,一时心慌意乱,要去打听一个究竟。但是,不用去打听了——我托运的那口棺材仍在车上,它并没被人移动。(实际情况是:当时我没料到,已经铸成大错。我正在运走一箱枪支,是那年轻人来车站给运往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一家来复枪公司的,而他却换走了我运送的尸体呀!)就在这时,列车员高呼“都上车呀”,我就跳上快车,很舒适地坐在一张圆背座位上。捷运公司收发货物的工人正在那里卖力地干活——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年龄约五十岁左右,看来是那么朴实、诚恳、和蔼,处处显得轻松活泼、劲头十足。车开出后,一个陌生人闯进了车厢,把一包早已发了酵、气味特别浓的软干酪放在棺材(我运的那箱枪支)横头盖上。也就是说,如今我才知道那是林堡软干酪,但当时我从未听说过那玩意儿,当然也就完全不知道它的特色了。再说,我们的车在茫茫黑夜中疾驶,强烈的风暴越吹越猛,我逐渐产生了一种愁闷苦恼的感觉,我的情绪开始低落,不断地低落!老工人轻松地谈了一两句有关暴风雪和严寒的天气,砰地关上了他那边的推拉门并且闩好,把窗子也给关紧了,然后四下里忙来忙去,把一些东西整理好,一边自得其乐地哼着小曲儿“美好的未来”,轻声轻气,音调很平板。过了不多一会儿,我开始觉出寒冷的空气中飘来一股极其刺鼻难闻的气味。这使我变得心情更加抑郁,因为我当然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我那可怜的亡友。他是在用这种凄恻无声的方式使我想念到他呀,此中含有无限的悲哀,于是我忍不住要落泪了,我因为那老工友在一旁而感到不安,我怕他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他继续悠闲自在地哼着小曲儿,一点儿没什么表示;我对此感到宽慰。宽慰吗,是的,但仍然心神不定;又过了不久,每过一分钟,我就变得越发心神不定,因为每过一分钟,那气味就变得越发浓烈,也就越发臭得令人难以忍受。又过了一会儿,工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按自己的意思整理停当,然后取了一些木柴,在他的炉子里把火烧旺。这使我说不出的苦恼,我只能认为那样做是一个大错。我肯定那会给我可怜的亡友带来有害的影响。汤普森——工人叫汤普森,我是那天后半夜才知道的——这时在车里到处搜寻,凡是他能无意中发现的隙缝,他都给堵塞起来,一面说,这一来,不管车外面是什么样的黑夜,都对我们无所谓了,他无论如何要让我们感到舒适。我没说什么,但相信他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对的。同时他仍像刚才那样哼着小曲儿;同时那炉火也越烧越旺,车厢里也越来越闷。我觉出自己面色苍白,开始恶心,但是一句话不说,只默默地伤心。不久,我留心听到“美好的未来”的歌声逐渐变弱了;随着就完全停止了,四周笼罩着预兆不祥的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汤普森说:
“呸!我想它该不是我生火炉用的玉桂皮树枝吧!”
他咳呛了几声,然后朝那口棺……那口枪支箱……走过去,对着下边那包林堡干酪停下,站了一会儿,又走回来,在我身边坐下了,显得深有感触。经过一阵沉思,他向那箱子做了个手势说:
“是你的朋友?”
“是呀。”我叹了口气。
“他已经摆得烂熟[3]了,对吗?”
此后,大约有两三分钟,谁也不再说话,都在专心思考什么;后来汤普森提心吊胆地压低了声音说:
“有时候,吃不准他们究竟是真的死了还是没死——你瞧,好像是死了——身体还是温暖的,关节还是可以弯曲的——结果呢,虽然你以为他们死了,但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可曾死了。我车上就有过这一类的事情。这确实可怕呀,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坐起来直瞪着你!”接着,稍停了一会儿,他微微抬起胳膊肘对那口棺材说:“但他不是在显灵!不是的,老兄,我可以为他担保!”
我们坐了片刻,一面默默地沉思,一面留心听那狂风在呼啸,火车发出隆隆响声;后来,汤普森感慨万千地说:
“咳,我们都得走的,这可是没法回避的。人为女人所生,日子短促,像《圣经》里所说的。是呀,不论你怎样看待这件事,它是十分严肃的、奇怪的:没人能回避它;所有的人都得走——你可以说,确实是每一个人。今天一个人还是精神抖擞,身强力壮……”刚说到这里,他急忙站起身来,砸碎了一块窗玻璃。把鼻子伸出去了一会儿,然后又坐下了。而我也使大劲站起身,在同一个地方把我的鼻子凑了出去,每隔一会儿工夫,我们就这样重复一次……“第二天他就像草那样被割下,而那些地方的人,原先知道他的,此后就永远不再知道他了,正像《圣经》里所说的。是呀,真的,这是十分严肃的、古怪的;但是我们都得走,迟早总有那么一天;这可是没法回避的。”
他又停顿了好半晌,接着说:
“他是生什么病死的?”
我说不知道。
“他死了多久了?”
为了迎合他可能的想法,更识时务的办法看来应当是夸大其词,于是我说:
“有两三天了。”
但是这一说反而弄巧成拙;因为汤普森听后露出了一副受骗的神情,那明明是在说:“你意思是说两三年吧。”接着他只管自顾自地说下去,若无其事地不去理会我所说的话,反而长篇大论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说日久不安葬死者,这有多么愚蠢。然后他懒洋洋地向那箱子走过去,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突然小跑步回来,跑到那破玻璃窗前面,说:
“如果早在去年夏天就把他运走,那在各方面都是一件大好事。”
汤普森坐下了,用他那块红绸手绢儿紧捂住他的脸,左右摆动着身体,像一个人正在竭尽全力忍耐着那几乎无法熬受的痛苦。这时那股香味——如果你可以管它叫香味的话——尽你所能想象的程度,正要使你窒息而死。汤普森脸上现出一片死灰;我知道自己已面无人色。稍停,汤普森把脑门子磕在左手掌里,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把他那块红手绢向棺材那面挥了挥说:
“这样的人我运过许多——其中有的也是摆得太久了——可是,我的老天爷,这个人胜过了所有其他的那些人!——轻易地胜过了他们。上尉,跟他相比,那些人只能算得是根缬草!”
他这样器重我那可怜的朋友,即使在那愁苦的情况下我也感到快慰,因为听来那完全是出于一种赞赏的口气。
稍后不久,显然我们必须采取一个办法了,我提议吸雪茄。汤普森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
“这也许可以把他的气味冲淡一些。”
我们兢兢业业地抽了一会儿烟,极力想象那情况已经好转。但是,毫不济事。过了不多一会儿,两人不约而同,两支雪茄同时从我们已经麻木的手指间悄悄落下。汤普森叹了口气说:
“不成,上尉,一点儿也没把他的气味冲淡。事实上这样一来反而更加糟了,因为看来是招恼了他。现在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办好?”
我想不出任何办法;真的,当时我只顾大口地咽气,不敢张开嘴说话。汤普森心烦意乱,无精打采,开始东拉西扯地谈论这一夜可恼的遭遇;提到我可怜的朋友时,他用了各种头衔——有时候是军衔,有时候又是文职称呼,我注意到我朋友的影响在很快地增强,而汤普森就将他的级别相应地提升——授予他一个又一个更高级的头衔。最后他说:
“我有一个主意了。咱们是不是拼一次命,把上校推动一下,推到车厢的另一头?——假如说,移过去大约十英尺。那一来他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劲头了,你以为怎样?”
我说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我们在破玻璃窗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打算憋着那口气,直到把这件事做完;接着我们就走到那里,朝那包害人的干酪俯下身子,紧扳住棺材。汤普森点了点头,意思是“准备好了”,然后我们使足了力气向前推;可是汤普森滑了一下,一跤栽倒,鼻子磕在那干酪上,一口气再也憋不住了。他一下子哽住了气,直作呕,挣扎着爬起,向门口直冲过去,双手在空中乱抓,沙哑着嗓子说:“别挡着我!——给我让开路!我要死了;给我让开路!”到了外面寒冷的连廊上,我坐下来,有一会儿工夫搂着他的脑袋,他清醒过来。紧接着他说:
“你以为那是因为咱们稍稍惊动了将军吗?”
我说没惊动他,我们并没移动他。
“嗐,这样看来,那主意又泡汤了。咱们必须另想一个办法了。我看,现在这个地方对他挺合适;如果他认为是那样,而且已打定主意,不愿意被人家干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