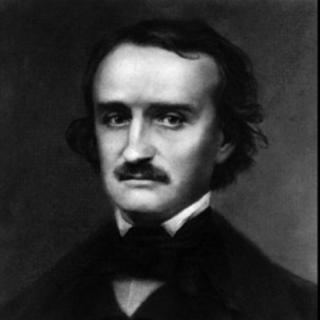
介绍:
我要写下的事是最疯狂却又最平常的,估计不会有人相信,我也不要求谁相信。连我自己的感官都拒绝证实的事,我如果还希望别人相信,那我肯定是发了疯。不过,我并没有疯,也绝对肯定没有做梦。但是,我明天就要死了,今天想卸下这副灵魂的重担。我的直接目的是把一连串家庭琐事简单明白地摆到世人面前,不加评说。这些琐事的后果曾经令我恐怖,折磨过我,也毁灭了我。不过,我不想解释。这事除了恐怖没有带给我别的,而它在许多人看来则似乎更多的是荒谬,而不是可怕。说不定今后可以发现某种智能,更冷静、更合逻辑(远不像我的智能那么冲动),能把我的幻觉转化为平常的事实,能从我惶惑讲述的情况里看出:那只是一串最寻常、最自然的原因与结果而已。
我从幼儿时代起就以性格温顺善良引人注意。我的软心肠太明显,甚至使我受到伙伴们的揶揄。我特别喜欢动物,我的父母也娇惯我,给我弄来许多不同的宠物。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宠物在一起度过的。我最高兴的事就是饲养和抚摩宠物。我性格里的这一特点随着我的成长而加强了,在我成人之后,它也成了我快乐的主要源泉。凡对忠实聪明的狗产生感情的人,我也很容易对他产生感激之情。这种感情的性质和它的强烈程度是容易理解的。对于经常有机会慨叹人类友谊之可怜、人类忠诚之淡薄的人,动物的这种自我牺牲的无私的爱,总能直接触动他的心灵。
我结婚很早,因为发现妻子也有一种跟我十分默契的倾向而感到高兴。她注意到我偏爱宠物,便不错过一切机会弄来些最可爱的宠物。我们家养着鸟、金鱼、一条很好的狗、几只兔子、一只小猴子,还有一只猫。
那猫特别大,特别美丽,全身纯黑,惊人地懂事。我那内心里带有不少迷信色彩的妻子谈起它的聪明时,老爱提到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全黑的猫都是妖巫装扮的。我提到这事,只不过因为此刻偶然想起,并没有更好的理由,并非说她这话有什么严肃的寓意。
这猫叫普路托,是我喜欢的宠物,也是我的游伴。我亲自给它喂食;我在屋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它都跟着,哪怕是上街,想不让它一直跟着也都困难。
就这样,我们的友谊坚持了好几年。可在这几年里,说来脸红,由于酒精这恶魔的影响,我的脾气和性格整体地出现了剧烈的恶化。我堕落了,一天比一天阴沉了,易怒了,不关心别人的感情了。我对妻子说些过头的话,后来甚至对她使用了家庭暴力。当然,几只宠物也深受我这脾气变化的影响,我不但不理它们,甚至还虐待它们。不过对普路托我还保留了足够的关心,没有虐待它。而在兔子、猴子,甚至狗由于偶然或出于喜欢而妨碍我走动时,我却是毫无顾忌地虐待。这毛病在我身上生了根——还有什么比嗜酒更严重的病呢!最后,连普路托也开始感到我这恶劣脾气的后果了。它现在老了,脾气也大些了。
有天晚上,我在城里一个常去的地方喝得烂醉回家。在路上我幻想那猫见到我就逃避,便揪住了它。它因我的粗暴,一时害怕,便在我手上咬出了个小小的伤口。魔鬼似的暴怒立即抓住了我,我完全丧失了理智,我原有的灵魂似乎立即离开了我的身子,一种比妖魔还凶狠的、被酒精哺育的情绪激怒了我身上的每根神经。我从外衣口袋掏出一把铅笔刀,打了开来,一把揪住那可怜的动物的脖子便从它眼眶里恶意地剜出了一个眼珠!现在我写起这该死的暴行也不禁脸红、发烧、心里颤抖。
早上我从昨晚为非作歹的恼怒里醒来,恢复了理智,才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一种半是骇然、半是悔恨的情绪。不过,那最多也只是一种轻微的、模糊的感觉,并没有触动我的灵魂。我又放纵了起来,很快就用酒把有关的回忆淹没得干干净净。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