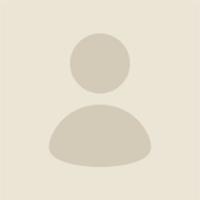
介绍:
冬至的记忆
作者:锦水微澜(辽宁)
制作:酷本
冬,终也。
至,到也。
冬至是最后的季节最冷时段到来之意。
但二十四节气在冬至后还有小寒大寒,所以可以猜测冬至的测立在小寒大寒之前,也可以猜测,在原始条件下,二十四节气的测立确定是渐进的不断完善的过程。
小时候,冬至的记忆是模糊的,冬的记忆是主要的。那时的冬天真冷,风大雪厚。地冻得裂纹,最大的开裂有二三寸宽。
天崩是传说,地裂却是真的。
小孩子看了心里害怕。大人怕孩子崴脚总是领着小孩绕开走。
那时的北风不但力大,而且会叫。
夜里躺在炕上经常听到它吹门吹窗的怪叫。
有时早上起来,门被雪埋得推不开,得外边有人帮忙铲雪才能出门。
门外的雪象大块儿的发糕一样厚而松软,院子里拳头厚的雪踩上去印迹清楚,谁家起来后去了哪里一望便知。如有去抱柴的,
有去茅厕的,
有去猪圈的……
墙角处的雪总是被风堆得最厚,一尺的厚度哪年都有几回。
小孩子淘气,一脚上去,鞋没影了,裤子上也沾了很多雪。
鞋湿了,放在火盆边上烘着。小孩子就只能在炕上玩耍,记得最清楚的是,用嘴在满是冰霜的玻璃上“呵”出一块透明,然后一只眼贴近窥视外面的世界。
那时,我家在农村。
冬至的含义不断清晰是下乡以后的事了。
农村明白节气的老年人多一些,言谈话语之间知道了“冬至长,夏至短”,“冬在三九,夏在三伏”等说法。
当时的农谚也对了解冬至有些教益,比如“小寒大寒,完了过年”。“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黄牛遍地走”。
开始以为“黄牛遍地走”是耕种之时拉犁的黄牛。后来有人告诉我,此“黄牛”是土名叫“草爬子”的一种惊蛰后最早醒来活动的草虫,而不是拉犁驾车的黄牛。
等到七九八九的时候,山下河里依然冰封,天空也没有大雁飞过。问老农怎么回事,人家告诉我说,“七九河开河不开。八九雁来雁不来”。究竟为什么,他们说历来如此。
突然有一天想明白了这件事:农历节气的确定是以长江黄河流域的气候为依据的 ,随着纬度升高,节气的农谚有变化是老百姓实践的总结 。此节气歌到了黑龙江有些地方就更对不上牙了。
中国幅员辽阔啊!
冬至之后,光照时间一天比一天长。“长”的感觉要许多天才明显体现出来。战天斗地时,我问过老农,一天长多少?答曰:一天长三刻。三刻是多少?答曰:钟摆的三个来回。正确与否,不得而知。
那时钟表在农村是稀罕物,几十户人家有钟的大约七八家,手表两只。计时的习惯分“鸡叫”,“晌午”,“晌午歪”,“头晌”,“下晌”,“傍黑”,“掌灯”,等等。精确的计时在生活中是没有意义的:敲铁钟上工,看日影歇崩。因此,钟摆三五秒的时长是没人注意的。
直到离开农村,三刻的时长也不知是多少。
很多年以后百度告诉我,每天长时为90秒。
至此,三刻的时长算是有了答案。
冬至的记忆,主要是童年和下乡时的记忆。那时的原始与朴素,火热与激情,早就成为往日的音符,或称生命的足迹。虽然如此,想起来还是真有点亲切甜蜜的感觉,尤其是一个人静静得闲的时候。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