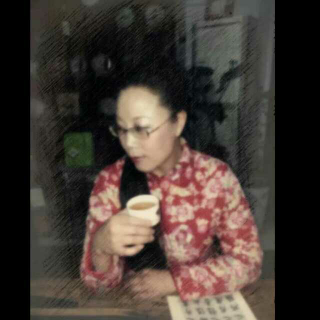
介绍:
灯节的灯 文/沈从文
元宵主要在观灯。
我生长的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一万户口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逢年过节,各街坊多有自己的灯。
由初一到十二叫“送灯”,只是全城敲锣打鼓各处玩去。白天多大锣大鼓在桥头上表演戏水,或在八九张方桌上盘旋上下。晚上则在灯火下玩蚌壳精,用细乐伴奏。十三到十五叫“烧灯”,主要比赛转到另一方面,看谁家焰火出众超群。
我照例凭顽童资格,和百十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城厢内外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灯的不仅要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坪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
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有时自告奋勇帮忙,许可拿个松明火炬或者背背鼓,已算是运气不坏。因为始终能跟随队伍走,马不离群,直到天快发白,大家都“烧”得个焦头烂额,筋疲力尽。
队伍中附随着老渔翁和蚌壳精的,蚌壳精向例多选十二三岁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当,老渔翁白须白发也做得俨然,这时节都现了原形,狼狈可笑。乐队鼓笛也常有气无力板眼散乱地随意敲打着。
有时为振作大伙精神,乐队中忽然又悠悠扬扬吹起“踹八板”来,狮子耳朵只那么摇动几下,老渔翁和蚌壳精即或得应着鼓笛节奏,当街随意兜两个圈子,不到终曲照例就瘫下来,惹得大家好笑!最后集中到个会馆前点验家伙散场时,正街上江西人开的南货店、布店,福建人开的烟铺,已经放鞭炮烧开门纸迎财神,家住对河的年轻苗族女人,也挑着豆豉萝卜丝担子上街叫卖了。
有了这个玩灯烧灯经验底子,长大后读宋代咏灯节事的诗词,便觉得相当面熟,体会也比较深刻。例如吴文英作的《玉楼春》词上半阕:
茸茸狸帽遮眉额,金蝉罗剪胡衫窄,乘肩争看小腰身,倦态强随闲鼓拍。
写的虽是800年前元夜所见,一个小小乐舞队年轻女子,在夜半灯火阑珊兴尽归来时的情形,和半世纪前我的见闻竟相差不太多。因为那800年虽经过元明清三个朝代,只是政体转移,社会变化却不太大。至于解放后虽不过十多年,社会却已起了根本变化,我那点儿时经验,事实上便完全成了历史陈迹,一种过去社会的风俗画。
边远小地方年轻人,或者还能有些相似而不同经验,可以印证,生长于大都市见多识广的年轻人,倒反而已不大容易想象种种情形了。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