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播客
打开APP

79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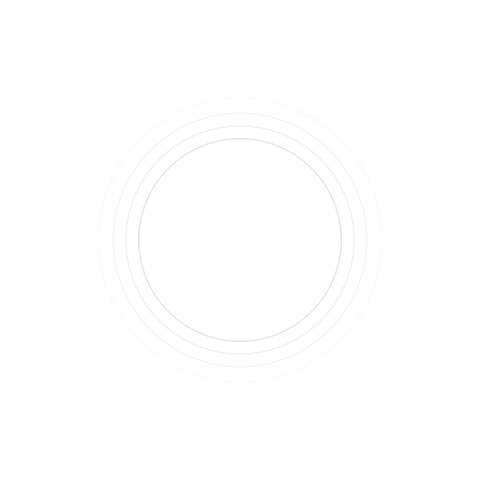
018. Ellen的德国摸鱼全记录
254
0
2021-09-23
题图:Ellen拍摄的第69届柏林电影节现场
嘉宾:Ellen
主播:7君 | 啊蹦
本期节目,你将听到可爱的Ellen和我们一起聊:
|工作两年,留学德国
|柏林电影节的现场采访报道
|翻译德语教材,获得一大桶金
|为中国播客行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以下内容,来自Ellen的公众号「肘子的城堡」
德国生活AB面
20/06/2021
某个周末,看了《无依之地》。本以为华人导演拿奥斯卡的故事会被国内津津乐道,消息竟然在微博被限流,“人之初,性本善“的发言也无处可寻。影片结尾的致辞是:献给那些不得不上路的人,肯定是巧合的是,剧中女主的名字叫做Fern,在德语里面正是远方的意思。
Fern在失去工作和爱人之后再也无法重回往日的生活状态,她说:“I maybe spent too much of my life, just remembering”。这让我联想到18年11月,来到德国的第一次旅行,我去到了亚琛附近的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叫做蒙绍(Monschau)。为我和朋友提供Couchsurfing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德国女士,她在当地的一个小学当老师,拥有一座三层楼带花园的独栋洋房,和丈夫已经离婚,家中虽然有三个小孩,但都成年搬出去住,算是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夜很深了,她依然拉着我们不停地诉说她的一些苦闷,比如在学校不被尊重,被学生辱骂但是无法回击,比如工资太低,但是为了退休金,只好忍耐。终于说要休息了,我和朋友正打算整理沙发准备休息,她却示意她来睡沙发,让我们上楼睡宽敞的房间。原来,一直以来家里有一只金毛陪她,但是一个月前它去世了。现在只要一上楼,她就会想起狗和她相伴的日子,所以她选择一直睡在沙发上。就这样,我唯一的一次Couchsurfing,变成了Bedsurfing。
过于沉湎在回忆中,会影响当下的生活;回忆也会失真,如若不能妥帖的记下,便会面目全非,又或者被完全遗忘。经历过聚会狂欢后面对空荡的房间的失落,结束一段精彩旅程后的怅然,对一段自由快乐时光的怀念,都需要找一些地方安放。
虽然略显粗糙和混乱地把在德国的一些故事分成了A面和B面,但真实的生活永远是多面的。往后的日子里,一定还有CDEFFG等多面的回忆跳入脑海,等待被诉说或者被记录。
A面
初入学的时候,有一次去欧盟议会学习的机会,但是经费有限,只有10个名额,系里直接把名额给了班里的奖学金生。虽然官网明确规定了项目奖学金遴选有语言成绩的要求,但是实际的发放却主要看DAAD和这些国家的亲疏关系,有些同学成绩和表现并不达标,却能依然获得不菲的奖学金,占班级大多数的非奖学金生(是的,花了巨资来读研的!)已经颇有微词,现在课外项目的机会更是直接给予奖学金生,显得更加不公。
于是,在入学的第一个月,整个班级就对系里提出了抗议,要求慎重考虑额外学习机会的分配。这是一次对权威的小小挑战,经过沟通,最终去欧盟议会的项目以抽签的方式分配给班级成员,而剩下的人,学校则拉来了一个新项目以安抚“军心”。
Esraa来自巴勒斯坦,是班里唯一一个戴头巾包住全身只露出脸的姑娘,与她同窗的时光里,从未得以见到她的发色。起初上课时,我们坐得比较远,很少交流。有一天课间休息,她出教室门,经过我背后,看到我在刷BTS的视频,一把抓住我,激动地说,你是army! 其实当时我只是不小心刷到了他们的帖子而已,深入交流后,又发现我们在追同一部韩剧,激动不已。就这样,韩流破除了次元壁,拉近了我们俩的距离,让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Khaled来自叙利亚,是一位难民。战争前的他曾是一名英语老师,友好但寡言。简单谈及他的流亡经历,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他是从土耳其走到德国的。一年后,他的哥哥,一名律师,沿着同样的路同样的方式也来到了德国。
一堂分组作报告的课,上课上到一半,来自苏丹的Muhammad突然站起来说,不好意思同学们,我今天需要提前离开,我要去隔壁联合国为我的国家抗议(当时苏丹发生了严重暴力事件),大家下课了感兴趣可以加入。晚上,我在网上流传的视频里,看到了他和他同伴们正在高声抗议国际组织的不作为。
最后一个学期,多了一些参与和组织会议的机会。当时的我被分在互动组,需要策划参会者的互动环节。根据当时的主题,我和Thy策划了一个闯关问答游戏,简单来说就是所有人起立回答问题,答错者坐下,答对者继续站立闯关回答下一个问题,最终获胜者可以拿到奖品。本以为可以非常顺利地完成互动,没想到在会议开始前,来了一位坐轮椅的观众。
我看到了他,却未产生任何想法,直到和我搭档的Thy主动和会议的主持人说明了这个情况,临时把活动改成在座位上举手回答。当时的我,还为临时的改动以及可能出现混乱而有些担心,然而活动开始,那位坐在轮椅上的观众热忱地参与着答题,整个互动环节虽然有些混乱,但是依然达到了热场的效果。我为我一心只顾效率和结果而感到一丝羞愧,也庆幸改了活动形式让坐轮椅的他也能获得参与的机会,细微之处得见对人性的照拂。
研讨会主题是德国与巴西的合作,主持人与嘉宾约好提前过一下之前发给他们的采访问题。德方嘉宾早就打印好了问题列表,拿了出来。巴西嘉宾非常悠闲地说,问题?什么问题?德方嘉宾说,没事,我把你的问题也打印了一份。️
B面
摸鱼无国界。
某日,课程内容为Fact Check。主讲老师让大家打开了她所负责的一个校友网站项目,让我们注册。于是,我们先花了20分钟,等所有人调试网络,注册,填写个人信息;之后,老师又让我们去参与网站论坛的话题,在“Heimat(家乡)”话题下发表自己认为的家乡是什么?虽然大家一脸懵,还是认真地去话题下刷起了留言。又20分钟过去了,以为老师会开始讲media research的内容了,结果她又让每个人依次读一下自己写的内容。对的,你没有看错,她让班里二十多个人,每个人一一读自己写的“家乡是什么”。剩下的40分钟里,所有人带着迷茫和疑惑,读完了自己的评论,每每读完,老师总会满脸微笑地点头说:好,很棒,非常美。等所有人读完,这一节课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于是老师清了清嗓子说:bis nächste Woche(下周见)。
硕士项目的入选条件中有一条是媒体行业相关从业经历,但是Amina可是实打实的professor,她入学前已经是孟加拉国一所大学的助理教授了。Amina的英语说得不太清楚,德语也不行,一到上课,总是穿着纱丽服,静静地在课堂角落坐着。她得到了DAAD的奖学金,但是需要在一年内考出德语B2证书。第一学年的课程简直是地狱模式,我们从周一上到周五,每天从10点上到下午4点,作为普通学生已经感觉疲惫,更何况她还要备考德语,兼或听到她还要处理找房子等等事宜。她一直在努力地备考,却总是失败。在后来的了解中,我还知道她的丈夫早在几年前因意外去世,她和她的儿子相依为命。课程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对孩子的想念,把她压垮了,在来到德国的第一个冬天,黑夜漫长无止尽,她患上了抑郁者,甚至无法正常入睡和进食。之后她就不太来上课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暂停了学习,回到了孟加拉国,回到了孩子身边。再后来,我看到她在脸书上分享的图片,有和孩子的幸福时光,有和学生的快乐出游。在疫情开始前,她来波恩参加了学术交流,与我们重聚,喜笑颜开,状态非常好。
上新闻学课程,主题是三分钟介绍本国的民主。系主任一旁听到我们的讨论,脱口而出,中国的民主,3分钟,太长了,1分钟就行了。
那场德国和巴西的研讨会,德方代表是一位资深记者和拉美地区专家。这是一场在德国的会议,但是她却在会议中间经常不顾听众飙西班牙语,顾自和来自墨西哥的男主持人讨论问题,把非洲妹子主持人晾在一边。活动结束,她离场,经过我和两个东南亚妹子。或许是因为我们都长着亚裔面孔,她突然用西班牙说了一句“are Chinese still alive?” 她并不知道,我身边来自泰国的姑娘西班牙语水平接近母语。
戴着口罩,经过火车站附近,想到国内的疫情,不愿在人多的地方逗留,我和朋友便加快了脚步,一群年轻人吹着口哨,哄笑着对我们大声叫喊“Corona”。
过了几天,全城禁止娱乐开趴,和朋友散步经过一个居民区楼下,楼上传出音乐声和欢闹声,几个年轻人趴在栏杆上,看到长着亚裔面孔的我们,戏谑地对着我们叫道:“Corona”。
答辩结束,我来到北德的朋友家小住,和她说好要体验德式生活。刚从树上摘下的苹果,我转身要去清洗,她制止我说,不用洗的,这是最自然的。参观她的菜园,她拔起一根胡萝卜,上面还带着泥,便要往嘴里送。我问,你不洗一下么?她答:it’s all vegan.
评论
暂时没有评论,快下载荔枝app抢沙发吧!
00:00
7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