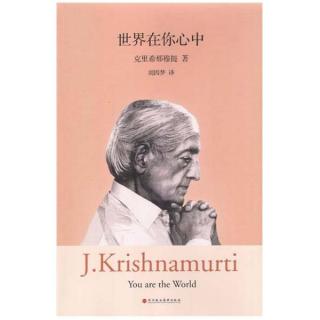
介绍:
问:我有一个问题现在必须提出来。觉察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您为什么说这是件很困难的事。如果你正在进行一项很难的差事。在不运用意志力和信心的情况下,你的行动基础是什么,要如何持续下去?
克:我想我了解你的意思是什么。你想问的是:“什么是觉察,觉察跟行动有差别吗?”先生,这是不是你要问的?
问:不,我的问题是:你所从事的这项活动是枚关生死的。你要如何在你的生命中找到这股力量,来从事某个能够让你存活下去的特定工作?
克:我了解了。你是想问,在何处能找到这股能量,找到这股让你正确存活下去的能量?对不对?
问:是的。如果你的行动是出于无界分的自性,那么你即使不运用意志力,行动也会产生。
克:一点也不错。
问:(没有被记录下来)
克:先生,我了解。但是,你如何能不运用意志力而活―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对立。你如何能毫无冲突地活着而同时又能立即行动?
问:我可以选择死亡。
克:你不能选择死亡,你必须活着⋯⋯
问:那问题就在于怎么去做了!
克:等一等,先生。你刚才问:你能通过什么方法,活得毫无矛盾,活得积极,随时处在觉察的状态生里。这是不是你的问题?首先,我们所谓的觉察到底是什么?我现在不是在提供意见,我是在观察事实。觉察是不是一种累积知识的过程,然后我再从这些知识中采取行动?这是否表明,我储存了许多的经验和记忆,然后我从其中采取行动?还是,觉察乃是一种不累积任何东西的认识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让我们来慢慢地探讨。并不是我先学会了某个东西,然后再按照我已经学会的东西来采取行动,而是学习就是一种行动,学习就是一种行动。你虽然想知道该如何面对恐惧,该如何生活。但如果你通过一个方法来告诉自己如何生活,就是在臣服于别人创立的某种方法。这么一来你就不是在觉察了,而是在臣服,按照某个程序在行动。其实,这根本不是行动,而是模仿。因此,你如果了解了某个方法及体系的内容,然后你就能察觉自己正在做什么,这份对人生的觉察便是真正的行动,我有没有把话说清楚?其实生活、觉察及行动是息息相关的。
问:我不明白为什么分析是有害的事,这是一个很难了解的观点。
克:听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难道不累吗?
问:一点儿都不累。
克:一点儿都不累,为什么?(听众笑了起来)等一等,先生,你为什么不觉得累?如果你一直在用心聆听―我不是在批判你―你应该已经累了,对不对?
问:我不这么认为。
克:先生,演讲者一直在努力地解说,要想跟得上他,你也得付出一些努力才行。并不是“他在讲而你在听”,其实我们是在共同探索并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认清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你们坐在那里跟着我分析了一天,很显然你们的心已经累了,但是没关系,让我再深人地谈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演讲者说过,分析这个活动中包含很多东西―很显然时间是其中的一样东西。分析暗示着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来达成某件事。而且,分析者必须非常仔细地分析,否则他很可能会出错。若想正确地分析,分析者就必须摆脱掉所有的偏见、结论或恐惧。如果分析者在分析的过程中产生了扭曲的观点,那么这个分析者只会制造出更大的局限。我们之前解释过,分析者与被分析之物是没有区别的。一旦你了解了这一切―时间、分析的过程、你所下的决定、可能会阻碍你继续清晰地分析的结论,以及认清分析者即是被分析之物―你就永远不会再分析了。你如果不再分析了,就能直截了当地看事情,因为眼前的问题会变得非常急迫而强烈。这就像有一个人抱持着非暴力的理念,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变得不暴力,而不是如何从所有的暴力之中解脱出来。我们关心的只是如何在当下立即从暴力之中解脱出来,而不是明天才去做这件事。如果我们观察“分析”的整个过程―心理分析已经变成了时尚―并且认清了它所暗示的一切,你自然会拒绝它。当你否定了某个错误的东西之后,你就能自由地观察,继而看到真相,但你必须先否定那个错误的东西。
上一期: 自在聆听|晨读原著:T41: Be Where You Are-Comfortable with Uncertainty
下一期: GRACE AND GRIT 5.5 WHY WE SEPARATED FROM SPIRIT
下一期: GRACE AND GRIT 5.5 WHY WE SEPARATED FROM SPIRIT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