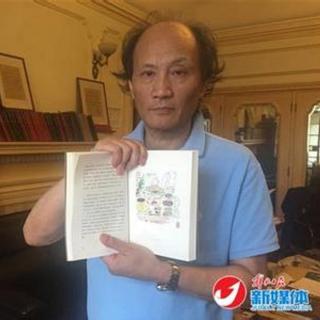
介绍:
广播专辑 繁花杂谈2 两重欢喜小说《繁花》
(2012-10-25 21:45:34) 杂谈
走在上海街头,有时候会突然驻足,努力回忆正踏足的繁华地,前身是什么样的?比如,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的巴黎春天,在成为巴黎春天前是什么?在记忆里已荡然无存。记忆如此残酷,连主人也一样欺瞒,所以有理由忧虑:我们后代以为的上海,就是陆家嘴?不要说在浓郁的上海气息里浸淫了数十年的我们的前辈了,我们也不同意。
说不很容易,请告诉我们什么是上海?当然,有不少作家喜欢书写上海,然而,他们的上海,纠缠抑或是拘泥于高档上海,和平饭店、新天地、愚园路……事实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上海人与和平饭店、新天地、愚园路无关,我奶奶1921年10岁的时候到上海,2006年95岁高龄在上海离世,在上海的85年中,没去过愚园路,没进过和平饭店,遑论新生的新天地和陆家嘴,她的上海会是什么样的?而她的上海,我以为是大多数上海人的上海。谁来记录大多数上海人的上海?此时此刻此境,金宇澄先生的《繁花》的出版,有横空出世的壮观。
壮观一词,首先可用来修饰《繁花》的体量。30万字,占用了大半本《收获》2012年秋冬期长篇小说增刊。在人人以写140字为限的微博为乐趣的当下,在人人以阅读几个字十几个字的微博评论为主打阅读对象的当下,能有勇气花2年埋首于一部30万字的巨制,佩服金宇澄的同时,为长篇小说的一次久已未有的成功感到高兴:阅读《繁花》的过程中,几次遇到有共通爱好的人推荐《繁花》。
壮观一词,其次可用来形容《繁花》里出场的人物数量。小说从澳门路写到莫干山路、康定路、皋兰路、高朗桥,对过去的上海稍有了解的读者知道,金宇澄的笔涉足了上海的上只角和下只角,要撑起这样的场面,得需要多少人物?100多个。值得钦佩的,就连蓓蒂和阿婆这两个笔墨很少、且来有影去无踪的小角色,都叫读者牵挂不已,更不要说小毛、阿宝、沪生、梅瑞、李李、汪小姐、陶陶、雪芝等等横跨文革、改革开放年代的主要人物了。
我则更青睐作家用文字记忆上海地域文化变迁的野心。
大概读过10页,我开始逢人推荐《繁花》。10页的时候,人物才刚粉墨登场,所以,10页《繁花》吸引我的,不是小毛、沪生、阿宝,而是我们久违了的只属于我们少年时代的上海气息。那时候,学生意拜师傅是这样的,少男少女中间交往的方式是这样的,楼上楼下邻居之间是这样窥私和暗通款曲的,下饭的这些菜肴家常却地域色彩浓郁,佐酒的通常闲话多于咸淡适度的小菜……家长里短、偷鸡摸狗,隐秘的情色男女、张扬的饮食男女。如果不是《繁花》,我这样的亲历者都几乎要忘却在上海盘桓了几十年也许上百年的只属于上海的气息!而今,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的确让我们过上了物质看似丰沛的日子,付出的代价是哪怕在上海开埠的原点,上海的味道也已荡然无存,我们的孩子不再会流利的上海方言,哪怕是杨浦上海话、复旦上海话、华师大上海话,这是上海味道快速流失的又一个例证,我们忧虑学校里本地孩子越来越少于外来人口的同时,是不是在忧虑上海将雷同于世界上每一座大城市?有心的金宇澄于不动声色中将30余年来上海惊心动魄的蜕变和丢失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是《繁花》给我的第一重欢喜。
第二重欢喜,是《繁花》的地图中心是西康路、莫干山路、康定路这一带。我家于2002年迁至此,对这一地域过往的了解仅限于:清晰的苏州河对岸曾是都市里著名的贫民窟,模糊的这儿那儿曾是面粉厂、棉纱厂,等等。金宇澄的细致,让我掌握了我家所在区域的变迁史。所谓热爱家乡,难道不应该从自己的居住地开始吗?
特别有意思的是,一部《繁花》用词没有一处来自有别于普通话的沪语,我却不由自主地要用上海话去阅读。用上海话读《繁花》,一定是金宇澄先生的期待,可不用上海方言却能引领读者用上海话阅读,这奇妙的效果怎么才能达到?我还好奇,如果一位不会上海话的的读者去读《繁花》,会读出与我不一样的味道吗?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