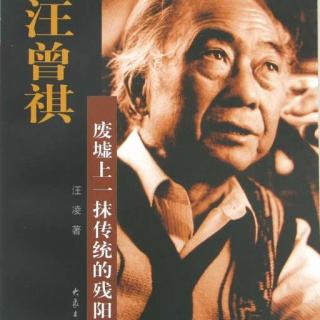
介绍:
他被誉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和从容。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和折磨,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以平静旷达的心态创造了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本期人物发现,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走进他的“凡人小事”。
汪曾祺, 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旧式地主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熏陶,对文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其大部分作品都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的小说多写童年、故乡,记忆里的人和事,在纯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波澜壮阔的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领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切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与高峰。
他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他的散文就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像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纯洁的爱情,正是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温馨、清雅。
汪曾祺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属科班出身。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他,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 “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努力建构作品的文化意蕴和美学价值,而不是一味追求新奇浮夸,反映时代的最强音
当今社会,由复制技术造成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相反,真正的美存在于个体生存中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包含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他的作品虽然间或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意趣,但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