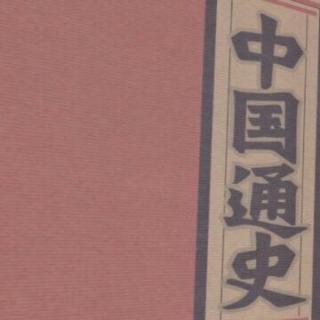
介绍:
孙周勇:我们正在做联合的研究,我们和哈佛大学的学者在做DNA的分析,也有学者将这一批石雕的人头像呢和阿尔泰地区、新疆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些同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根据石峁遗址年代特征,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们初步认定,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三百年的共存期。从目前对石峁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或该邦国当时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陶寺。如果说陶寺遗址是帝尧之都,那么在地理位置上与其极为相近的石峁遗址又该是谁之都或谁之聚落呢?根据《史记》、《汉书》有关黄帝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有学者提出,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认为石峁城址很可能就是黄帝或其后人的居驿。
邵晶:对于我们做考古的人来说是讲求证据的,因为把历史文献中的人物和考古学文化去对比,这个需要反反复复多重的论证,最强有力的证据才能去这么说,所以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些保留。
令人不解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石峁,同样面临突然衰落之势。那么,远古时,石峁先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这个曾经寿命超过三百年的石头城,又为何荒芜败落呢?最近,通过环境考古分析初步表明,石峁地区曾出现过冷凉干燥气候,即公元前2260年前后进入降温时期,气温大幅度降低,干燥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灾难,严重影响了当时粮食的生长,粮食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表现在考古学上是古文化遗址数量锐减,人口也大量减少,并发生大规模迁移。
赵志军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 副主任:石峁遗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石峁遗址所处的位置,它正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农牧交错带上,它比其他区域来说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要更明显更剧烈,反映更强烈一些,因此呢,石峁遗址的衰亡应该和当地的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孙周勇:石峁的人群,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这个(公元前)1800年前后呢,北方的人群可能是南下,可能发生了一次大的这种人口的迁移,现在还不能排除石峁和陶寺是两群人,就在晚期这个阶段,因为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交替过程,政权的更替。
邵晶:像这两件,这也是石峁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器物,这种器物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灰色的,也没有什么独特的选型,但是它的制料非常的特别,它是燧石制的,这种石头的硬度比玻璃还要高,切割玻璃都不成问题,石峁有大量的箭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燧石制的箭头非常多,在石峁几乎可以说遍地都是,你下一场雨,在田间地埂随处可以捡到,它有多大的威力呢,可以把人的脊椎骨射穿。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发生了外族入侵和内部的暴力革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的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40到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一幅恐怖场景。
何驽:以前我们发现的这种深缶的盆形鬲,裆部都是弧形的,而这一件裆部底下是一个凸底,像一个尖底一样,看看它的区别,带有凸底的这个特征是石峁的陶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陶寺陶鬲最大的区别,而这件鬲的发现非常有意义,说明了是谁在破坏陶寺中期的宫城,那么这些人往往很有可能就是对陶寺中期政权的推翻者、征服者,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这场来自族群外部带动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陶寺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终导致持续300年文明的陶寺城邦衰落,底层革命与外族入侵说成为揭开陶寺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
因为气候的巨变,位于中国版图西北部的陕西石峁人不得不弃城远徙,而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处于东南部盛极一时的余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个源于气候的大幅干冷,而另一个则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另一场突发自然灾难的降临。孙周勇:我们正在做联合的研究,我们和哈佛大学的学者在做DNA的分析,也有学者将这一批石雕的人头像呢和阿尔泰地区、新疆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些同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根据石峁遗址年代特征,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们初步认定,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三百年的共存期。从目前对石峁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或该邦国当时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陶寺。如果说陶寺遗址是帝尧之都,那么在地理位置上与其极为相近的石峁遗址又该是谁之都或谁之聚落呢?根据《史记》、《汉书》有关黄帝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有学者提出,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认为石峁城址很可能就是黄帝或其后人的居驿。
邵晶:对于我们做考古的人来说是讲求证据的,因为把历史文献中的人物和考古学文化去对比,这个需要反反复复多重的论证,最强有力的证据才能去这么说,所以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些保留。
令人不解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石峁,同样面临突然衰落之势。那么,远古时,石峁先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这个曾经寿命超过三百年的石头城,又为何荒芜败落呢?最近,通过环境考古分析初步表明,石峁地区曾出现过冷凉干燥气候,即公元前2260年前后进入降温时期,气温大幅度降低,干燥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灾难,严重影响了当时粮食的生长,粮食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表现在考古学上是古文化遗址数量锐减,人口也大量减少,并发生大规模迁移。
赵志军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 副主任:石峁遗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石峁遗址所处的位置,它正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农牧交错带上,它比其他区域来说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要更明显更剧烈,反映更强烈一些,因此呢,石峁遗址的衰亡应该和当地的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孙周勇:石峁的人群,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这个(公元前)1800年前后呢,北方的人群可能是南下,可能发生了一次大的这种人口的迁移,现在还不能排除石峁和陶寺是两群人,就在晚期这个阶段,因为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交替过程,政权的更替。
邵晶:像这两件,这也是石峁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器物,这种器物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灰色的,也没有什么独特的选型,但是它的制料非常的特别,它是燧石制的,这种石头的硬度比玻璃还要高,切割玻璃都不成问题,石峁有大量的箭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燧石制的箭头非常多,在石峁几乎可以说遍地都是,你下一场雨,在田间地埂随处可以捡到,它有多大的威力呢,可以把人的脊椎骨射穿。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发生了外族入侵和内部的暴力革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的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40到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一幅恐怖场景。
何驽:以前我们发现的这种深缶的盆形鬲,裆部都是弧形的,而这一件裆部底下是一个凸底,像一个尖底一样,看看它的区别,带有凸底的这个特征是石峁的陶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陶寺陶鬲最大的区别,而这件鬲的发现非常有意义,说明了是谁在破坏陶寺中期的宫城,那么这些人往往很有可能就是对陶寺中期政权的推翻者、征服者,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这场来自族群外部带动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陶寺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终导致持续300年文明的陶寺城邦衰落,底层革命与外族入侵说成为揭开陶寺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
因为气候的巨变,位于中国版图西北部的陕西石峁人不得不弃城远徙,而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处于东南部盛极一时的余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个源于气候的大幅干冷,而另一个则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另一场突发自然灾难的降临。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