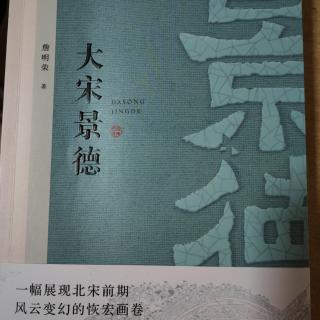
介绍:
元休看得入神了,仿佛一股清泉淌过他的心灵,他不顾一切往前挤……
后面的张耆慌了,他不敢离两匹宝马远了。他环视四周,突然看见场外树旁,一位蓝衣少年正对着他笑呢,夏守赟他们到了!他指指马匹努了努嘴,就往王爷方向去了。张耆心里有底了,他虽然年轻,但多年的历练使他的眼睛像鹰一样锐利,他已经觉察到场子里混杂着坏人。保护王爷就是他的天职。“公子小心!”张耆用有力的臂膀拨开人群,挤出空当,让元休挤到了台前。
刘娥饱含深情的说唱声与铃声鼓声的交响,震撼了全场……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刘娥举起鼗鼓腾空跃起,白裙完全展开,她上身后仰,轻盈地劈叉坐在台面,鼗鼓自然收回落在胸前丝线绣的牡丹花上,灵巧的右手仍在鼗鼓上拨弄。鼓声戛然而止。
台下响起一阵阵热烈的喝彩声。
刘娥宛如一只洁白柔嫩的天鹅仰卧在戏台上,忽然间,她向台前转过脸来,回眸一笑……
她明媚的目光刚好与韩王元休清纯的目光电火般相撞在一起,只一霎时,她已经意识到这位青年公子曾经见过。
元休只觉得心猿意马,他距台上的刘娥不足六尺,因为演出,她的眉眼是浓妆的,弯弯的眉毛下,卷起的上下睫毛将一双丹凤眼衬得如墨潭一般清澈,松明子灯在瞳仁处映出一点高光,下眼睑在光照下格外动人,形成一双极好看的蚕蛾;鼻子的线条坚挺高贵,灿烂无瑕的笑容绽放在丰盈的脸上,像熟透的苹果;下巴微翘,完美的曲线顺着白净的脖子延至胸前。
元休在宫里长大,皇宫佳丽何止见过三千,据说绝代佳人小花蕊夫人还抱过小时候的他。但是眼前她的妩媚娇美,只片刻便印在他心里了。
刘娥手一撑,已站了起来。她再次躬身作揖,但台下的喝彩声不让她退下去。她只好再次拨响鼗鼓,说:“那小女刘娥再说一段评书吧,《唐太宗求贤纳马周》。”
“话说大唐贞观改元,太宗皇帝仁明有道,信用贤臣……”刘娥踩着鼓点满台子转悠,略带蜀音的金嗓子娓娓道来。
这时,开场时敲锣的青年男子、刘娥兄长刘美,从台左侧走到台前,那面铜锣反过来,就成了一块铜盘,里面装着一条银链子,他躬了躬身子说:“我们是后汉右骁卫大将军刘延庆的后人,落难从蜀地来到京城。小妹刘娥的演唱承蒙大家捧场,敬请大家赏光。这根银链子送给捐钱最多的朋友。”说完,他将铜盘置于戏台前沿。
台前的人们有的从衣袖里摸出碎银,有的从布褡里拿出一吊铜钱,不一会儿,铜盘里就放了不少,有一位青年公子在铜盘里放了一锭五两白银。
“张耆,拿银子。”赵元休有点慌了,怎能让别人占先!
张耆赶紧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银锭足足有五十两,在灯下迸射出炫目的光芒。
赵元休接过银锭,端放在铜盘中。
刘美连忙拱手答谢:“谢谢公子!”
“好!”“好!”场子里响起雷鸣般的喝彩声。
满脸喜色的刘娥随着鼓点还在说:“马周在御前,口诵如流,句句中了圣意。太宗皇帝是言无不听,谏无不从。马周不上三年,便做到吏部尚书。”
刘美已将铜盘端在手中。
刘娥走到台前,一拨鼗鼓:“一代名臣属马周!”
刘娥放下鼗鼓,双手从盘中拿起银链,捧向元休,嫣然一笑:“公子请笑纳。”
银链放在赵元休张开的掌心上,他脸红了,竟痴痴地说不出话来。
喝彩声之后,人群渐渐散了。
张耆用一块手绢帮赵元休包好银链,放入怀中,说道:“公子,回去吧。明后天我们再来便是。”
刘娥将银锭揣入怀中,跟刘美进后台去收拾行装,她回过头来朝赵元休点点头。
赵元休魂不守舍地与张耆来到系马石桩前,张耆望见夏守赟还在不远处,就朝他眨眨眼,做了个手势,要他们远远地跟上。
一弯上弦月已经升起在树梢,向沃野洒下银辉。
总算找到她了,赵元休还沉浸在刚才的情景中。张耆牵着两匹马跟在后面缓缓沿着汴河前行。
隐隐约约,张耆听到传来鼗鼓声,他警觉起来。
鼗鼓声好像是在左前方树林里,断断续续,没有节奏,急促,紧张。
“给我!”赵元休抓过缰绳,纵身跃上芦花驹。
两人纵马飞奔,一阵风便冲进了树林中。
三个蒙面人正将刘美、刘娥围在中间。
刘美舞着一根扁担抵挡着。
短装打扮的刘娥背靠哥哥,一只手拿着鼗鼓准备还击,一只手捂住胸前的银锭。
“把银子交出来,就放过你们。”一位蒙面人拦住刘娥说。
“强人休得无礼!”冲在前面的张耆扬起短剑,紫电青光,刘娥面前匪徒的蒙面巾已被划开。
张耆俯身从鞍座下抽出一根水火棍,手起棍落,与刘美对峙的匪徒肩膀一斜,仰面朝天。
赵元休飞驰过来,芦花驹的铁蹄已将刘娥面前的另一匪徒踩翻。
“快走!”月色中,三个黑影落荒而逃。
赵元休已经下马,将刘娥扶起。
刘娥捡起一块玉佩,借着月光,读出声来:“韩王……”她大惊失色。
“哦,是我刚才打斗中落下的。”韩王赵元休笑着将玉佩按在刘娥手中说,“小王就送给你了。”
刘美一听是小王爷,赶紧跪地答谢:“小民刘美拜谢韩王殿下。”
“快请起,路遇不平,见义勇为乃正当之举。”元休说道。
张耆已将翻在旁边的一副挑担扶正,说:“刘美,原来你是个银匠,你们住在哪里?我们护送你们兄妹到家。”
“我们在外城贵仁巷租了房子,顺汴河走就到了。刚才是被他们逼到树林里的。”刘美挑起银匠担子带路。
元休见刘娥脚有点打软,就扶她上马。芦花驹太高,刘娥上不去,但很奇怪,芦花驹竟温驯地伏下了,刘娥伏在马脖子上顺势上了马鞍。
张耆牵着马殿后。
刘美说:“其实,这些人也不是什么江洋大盗,我认出他们就是这汴河边的市井泼皮。看见小娥喝彩人多,他们早就虎视眈眈,今天见王爷赏赐,遂见财起意,打劫我们。”
忽然,月光又隐进黑烟似的云影中,前面有一片黑松林,阴森森的十分可怕。
“不用担心,有我们在此,没人敢来欺侮你们。”元休安慰刘娥。
说时迟,那时快,林子里一下子闪出七人,手执木棍,将他们团团围住。为首的戴着面罩,但光头脑袋依旧在月下泛着白光。
“就是他们,我们将银锭拿到,就上瓦子大吃一餐。”那位蒙面巾被挑破的歹徒说道。
两人过来就要扯刘娥下马。
韩王就势蹲下一个扫堂腿,前面的人摔了个狗啃泥,后面那个人收不住脚,两人滚在一起。张耆从腰间摸出绳子,将这两人捆了起来。
为首的光头一扯面罩,举起棍子向韩王赵元休劈来,忽然斜刺里飞来一匹快马,黑暗中朴刀一挑,歹徒虎口震开,棍子已飞去天外。
“王爷勿惊,继忠来也。”
这边一匹快马已冲到最前面,夏守恩伸出手来,抓住一个歹徒的腰带,就势提了起来,重重地丢在地下。
夏守赟少年英雄,在马上朝两位歹徒一棍扫去。“哎哟!”两人应声倒地。
一名歹徒看清夏守恩他们的装束幞头,大叫:“不好!官府来人了。快走!”
刘美干脆放下挑子,拿出绳子绑了一个。
逃走二人,绑了五个。
刘娥揣着银子伏在马背上一下都不敢动。半晌才坐正身子,感慨地说:“这才见识了王府的英雄,迅雷不及掩耳就打败了强人。”
王继忠跃下马来,擒住光头。夏守恩、夏守赟兄弟过来,拜见韩王。
元休说:“三位辛苦了。”
夏守恩吩咐弟弟:“你留下吧,我与王给事将歹徒送开封府。”
张耆再找了绳子,将五名歹徒脚也串起来了。
王继忠扬起朴刀,对歹徒们说:“若想逃走,头就没有了。”
被反绑着手的歹徒全部跪下来:“将军饶命!”
夏守恩在马上牵着绳子串起一溜歹徒,王继忠手握朴刀押在后面,往开封府去了。
机灵的夏守赟过来,要为刘娥牵马。
“去去去!你没有看见我们要说话吗?”赵元休说。
夏守赟舌头一伸,做了个怪脸闪一边了。
刘娥向为她牵马的韩王元休诉说了她的身世。
赵元休说:“那天在码头接皇兄耽搁了,后来在新平瓷行得知你们的信息,找到外城又没线索了。过了数月,还是张耆看见了演出布告,才见到你。”
刘娥心潮起伏,这位为她牵马的英俊王爷就是普元法师料到的贵人吗?她的一生会因这纯情男子而改变吗?
她告诉韩王,那天他们兄妹从新平瓷行出来,在外城贵仁巷找到一处住屋就租下了,刘美打银器也有个接单的地点了。她在勾栏瓦子的场子里唱了一阵子,租金太高,场子又小,只适合坐着说评书,容不了她手执鼗鼓满场转。倒是一位老板带她到郊外平安里,让她在戏台上说唱,租金不贵,他们先交了二十两银子,然后买了几套行头就开始了。
贵仁巷在外城的城中村里,他们租的是一套厅堂带两厢房的屋子,还有个小院,倒也清静。
刘娥要进里间去为韩王烧水,几匹马在院外嘶鸣起来,这是一个信号。
张耆说:“如果内城守卫将城门关了,就回不了王府了。”
赵元休恋恋不舍跨上芦花驹,刘娥目送着他们消失在夜幕中,仿佛一切都在梦中,触到了怀中的银锭,才知道一切都是真的。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