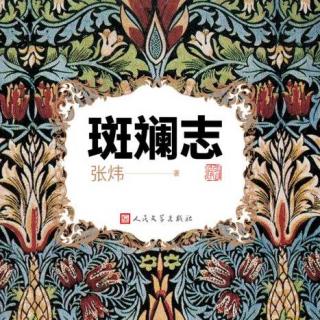
介绍:
我们发现,一个人的一生总有许多相逢和别离,在这样的环节中重复行进。不同的只是对这些环节的处理。在苏东坡这里,无论是分手还是重逢,都常有诗章往还。这里的“重逢”和“分手”是一个泛指,无论是山水、故人、路友、亲人、爱人,都在这个范畴里。每到了这样的时刻,他都会将一首诗交还对方。在今天的人看来,这可能是过于风雅或呆气的举动。如果现在的人重复这种动作,每每交出一首诗,我们会觉得他可笑、滑稽,或许不觉得有多么雅致。
在古代,不仅中国如此,域外也是如此。手边有一部日本的《源氏物语》,打开即可见到类似场景:两个人分手,一个会交给另一个人一首诗;男女相处常以诗往还。历史上那些诗人,比如李白和杜甫,都像苏东坡一样,是写别离诗的能手。中国唐代就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章,像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高适的《别董大》、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难以历数。有时我们甚至会将其当成一种惯性动作。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惜别之诗,可见在古人那里已成常态。
对比之下,我们作为现代人会觉得自愧不如,会觉得古人的情怀与生活真是别有天地,他们雅致极了浪漫极了。不过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真的不会觉得他多么有趣,一定会暗自发笑。是的,那曾经是中国文化人、仕人的一种惯性与天性,是他们的一种标准动作。我们静心思忖,甚至觉得一个地区如果交到这样的一群人手里,倒也放心一些,起码会少一些令人惊愕的粗野和蛮横。有那样的情怀和雅致,大概不会粗暴地对待黎民。柔细的心肠,婉转周密的思绪,会容纳得更多,安置得更多,关怀得更多。他们关切自然环境,也关切世道人心,所以我们更可以放心地将物事托付给他们。
不知从何时起,人和人之间的诗文相赠变得迂腐可笑起来,这值得好好研究一番。也许这就是野蛮通行泛滥的开始。我们假设社会管理者有诗之情怀,也必有一份缜密和悠远,会多少让人松一口气。
古人说的“文人多良吏”,其实大致在说“诗人多良吏”。因为当年他们最主要的书写形式是诗,仕人大致也是诗人。时过境迁,几百年几千年过去,生活急剧变化,让人既耳目一新又瞠目结舌。生活变得如此粗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了诗性。在官本位的社会传统里,治理者总是起到大榜样的作用,他们往哪个方向移动,往往是一种引领,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指标。胸无点墨的人相逢只会豪饮,只会留下宿醉与呕吐,哪里还可以指望他们作诗。
人的一生会有多少重逢,这在万水千山相阻隔的时代,相会与分别都变得格外珍惜。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主要原因当然还是古人更重情分。因为人与人的空间比现在大,他们相距遥远,“相见时难别亦难”。他们远远没有陷入今天的信息疲惫,所以关于彼此的一点消息都格外看重。/ 不能依依惜别,怎么会珍重生命,怎么会珍惜大地上的一切。相比来说,现代人更显得无情无义。
“举酒属雩yú泉,白发日夜新。何时泉中天,复照泉上人。”(《留别雩yú泉》)“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赠刘景文》)“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今天展读苏东坡的这些惜别之诗、酬答之章,会感到多么遗憾和惆怅。我们在心底呼唤那个时代和那片自然?不,我们是在想象中品味和描绘那份美好的情怀。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