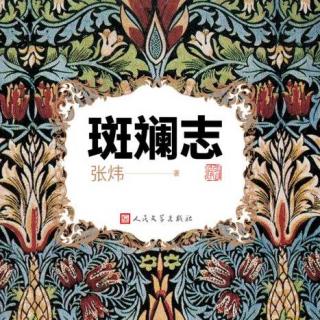
介绍:
初到贬谪之地黄州,苏东坡甚至没有落脚的地方,他只好借住在定惠院。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寺院里,他咀嚼着一切,享受难得然而又是陌生的孤独。这对一个热闹惯了、意气风发的诗人来说是少见的。在一场大难之后,他就像是被一只巨手轻轻一捏,放置在这个地方。这里有和尚,有禅意,有天籁的汇集。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回望和前瞻,这时候目光就变得深长了,所有景物都是另一番颜色,有的变得淡漠,有的愈加浓烈。也就在这样的时光中,他有一次闲步,在篱笆旁看到了一株开放的海棠。这让他有掩不住的惊喜,站在那儿久久不愿离开。就这样写就了一首题目极长而又绝妙的七言诗《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很显然,在诗中他以海棠自喻:“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他以为这海棠的种子是一只鸿鹄从天上带来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哪忍触。”
可惜他的名气实在是太高了,即使他深藏于寺院之中,也仍然有很多的人前来探奇,还得到了当地最高长官黄州太守的关照。这些人当中包括了武昌的王齐万兄弟、杭州的僧人参寥、云游四方的西蜀道士杨世昌、家乡老友巢谷、岐亭的陈季常,还有琴师崔闲等,都先后来到黄州陪伴他,有的甚至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
他仍旧无法寂静下来。他的寂寞和怅惘可能在友人离去、在半夜、在独自伏上窗棂观看满天星斗的时刻。由此可见人生寂寥不完全依赖身外,主要还是心内。一颗冷寂之心,即便是再大的热闹也不能剥夺,但这需要重大遭遇之后,需要巨幅的跌宕和震动结束。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没有人寻求这样的际遇。但它落在了诗人身上。生活中有多少人遭逢了这样的时刻?当然很多,他们这时可以回味,享受那种“失败的美好”。远离了胜利者的庆典,失败的那种苦涩,那种严厉的苦味,此刻却能泛出丝丝甜息。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收获更多的东西。失败比之胜利,竟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感”。这种优越独属特殊时段和特殊的人:尽可以一个人享受这时光,不需要他人帮扶、参与和陪伴。真实的孤单是无法陪伴的,没人能够进入他人心灵深处。这不仅是一杯苦酒,还是一杯烈酒,劲道之大足以让人久久沉醉,然后慢慢醒来。
一切不出所料,又出人意料,苏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三年,写出了著名的书法珍品《寒食帖》。有趣的是他还写了一首酒后晚归、敲门不应的小词,让黄州太守徐君猷大惊,误以为这位贬谪之人已经逃逸:“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关键两句是“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还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身为不系之舟,当然非我所有;难忘的“营营”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狗苟蝇营之“营营”,让诗人嘴角露出了不屑的一笑。皇皇大事却为“营营”,有趣而豪迈。这只有黄州的苏东坡才能说出,只有“醒复醉”的苏东坡才能感悟。他想起孔子的“乘桴浮于海”,想乘舟远逝,走向江海。余生如何度过倒也未知,但仍然要寻找落实,还是放逐到世外,都很难定。他到黄州的时候只有四十四岁,离开已四十九岁,而这五年恰是一生中少有的大安之期。他开始了长期定居于此的打算,他亲自设计的居所落成于大雪纷飞之时,故名曰“雪堂”。
他在《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写道:“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真是用心缜密,也获得了极大的欣悦。他说自己在这里可以“起居偃仰,环顾睥睨”(《雪堂记》)。这幢想必是美丽舒适的建筑落成之后,又在朋友资助下盖了三间瓦房,取名“南堂”。这个南堂也让他欢欣无比,他在《南堂五首·一》中写道:“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在这清闲安适之地,他的创作也达到了一生的高峰。他辛勤的开垦了黄冈东面的一块坡地,从此便有了“东坡居士”的名号。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头发已经全白,看上去真像是一个老人了,好像所有这一切,都强化了“晚年”这个意象。一家老少二十多口齐聚黄州,在这样的人生场景里,他更加相信自己是陶渊明转世:“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
名花独幽,芬芳扑鼻,香气愈传愈远,洋溢于天地之间。诗人在大跌宕之后有了更多的沉郁,也有了更广大的情怀,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最终成为古今两大豪迈诗文。从此他的写作进入了特殊的、不可取代的沉着期,而且有了更加深沉的著述心情。这意味着诗人走出了最大的苦境,也走向了更具意义的创造。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