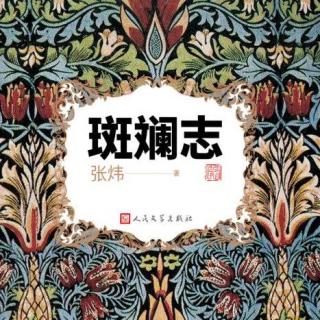
介绍:
对于自己无法改变的性格即命运,苏东坡当然是越来越清晰。而且我们相信他从政之初就并非模糊懵懂。他读到的历史文字太多了,知道历史上关于命运、关于坚持的种种结局。可是这一切都无法让他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他可以在岁月中不停地修葺,让其变得完美,却不是走向怯懦和孱弱。他的完美在于同理想的向度一致,而非其他。“多生绮语磨不尽,尚有宛转诗人情。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次韵僧潜见赠》)“从来性坦率,醉语漏天机。相逢莫相问,我不记吾谁。”(《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并引·三》)自我本如此,不管不顾自嘱自勉,自始至终。“不知下有行人行”,“猿吟鹤唳”,都出于本能。人在世俗之中时有醉语泄露天机,那仍然是自我的属性。醉语就是天真之语,是畅饮之后才有的。
苏东坡是俗语所讲的那种“直肠子”。“乌台诗案”后,他也曾经吸取教训,用力禁止自己的诗作流传开去,而且怯于动笔,但只过了很短的时间就“故态复萌”,仍旧大放心曲。官场上所习惯遵行的严谨和拘束,他远远不够,本来就是一个嘴巴不够严的人,还时有醉语。比如为了反对新法,他对皇上宋神宗恳切而激烈地进言,出门后却将皇上的赞赏讲与同僚,结果被政敌王安石等人加以利用,也引起更多人的提防。这种行为本来就是为仕之忌。他的这种不周与随性,当然是性格使然。其实这样的天性最不宜于从政,就像李白和杜甫不宜做官一样。这一类人最后投身于政界,对个人而言是一种大不幸,对国家而言则是一种大幸。
在宫廷这个密闭阴浊的小世界里,苏东坡这样的人等于是一束光。这个世界有另一种声音回荡,才会打破沉闷。可惜这样的地方从来容不得他们,就像冷漠容不得热烈,密闭容不得缝隙一样,这个地方最需要的就是一起窒息,从黑暗走向黑暗,最后再完结于黑暗。然而作为一个来自生机盎然的蜀地眉山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持续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必要把自小习惯了的那种生机和鲜亮,一再地移植过来。最后他只能成为一个流放者,被驱赶于野,去做他的野生之梦。就这一点来讲又成全了他的艺术,使他有了另一种收获,尽管付出太大。
就此,他对命运、宫廷、人生与社会,都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也就有了更大的文章。 与挥挥洒洒的尽情吟唱完全不同,从政之途实际上是一种藏锋之术、隐忍之术,在专制主义的“家天下”传统里就尤其如此。只有离开这条道路,那点“浩然之气”才会泛上心头,举步远途,感受扑面而来的“快哉之风”。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他将越发认定固有的追寻,惊讶自己居然忍下了那么多。一波又一波的追悔总是来得太迟,总是无法改变。
他和朝云生下的唯一的儿子使他欣喜不止,为此作《洗儿》一诗,吐尽委屈:“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人生坎坷归结于此,不过是一种无奈。他当然知道,一切都因为生命品质的不同,哪里是什么聪明和愚笨之别。他不过是用一种浅显平俗的语汇来发泄罢了,回答的也并非自己。诚实坦荡与阴暗狡诈的人性之别,同聪明与否没有更多的联系。强烈的诗性一定是热情的,而冷漠与镇定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处世的要求。善藏者不可以为师,因为他们不会将心曲吐个干净。一个人没有隐藏的角落,一切都倾吐净尽,摆在明处,当然是非常危险的。
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成名之后,历尽屈辱磨难,最后吐出了一句肺腑之言:“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我们”是谁,“他们”又是谁?这里既指向了某些具体的人,但又 / 不尽然。“他们”就是险恶、庸俗、普遍的人性的龌龊,而“我们”是一切明朗的人性,是生长的状态。“我们”当然属于所有的天才,“明处”和“暗处”的区别,注定了一切天才皆是悲剧。陀氏接着说:“那些折磨者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他们人多,而我们人少。”
改变一切的那只手,显然不在人间;它有更大的力量,它是一只无所不能的巨手。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