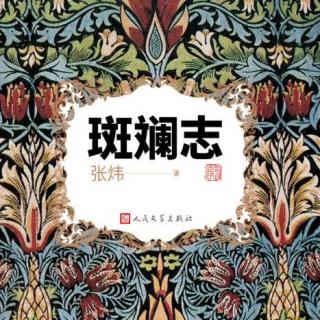
介绍:
历史上的“风流才子”太多了,这其中不乏自私狭隘之徒,他们将所谓的“才华”涂在表层,像一个符号和徽章一样顶戴身上招摇过市,实际是无足轻重的人生。这些“才子”不过是一些概念化的表演者,不会给世界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是划下一道道紊乱潦草的痕迹而已。这些生命是孱chán弱的,密集如蚂蚁,为口腹之欲碌碌奔走。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人物颇有欺骗力,因此也会取得丰厚的回报,获得一些机会。但假以时日,一切也就清晰了。这些人一度拥有了一切,什么名声和财富,应有尽有;但他们唯独缺少仁慈和怜惜,缺少最基本的正直。
苏东坡在任所上常常呕心沥血,操劳不已,有时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在凤翔,他为那些在激流中放木筏、常有生死之危的民工呼号不已;在密州,他面对铺天盖地的蝗灾欲哭无泪。历尽摧折之后,为了安度晚年,他反复奏请皇上才得以在常州定居,却因为一位老妇人的恸哭,白白放弃了花尽积蓄求购的一处房产。他的一生常常有“不忍”两字跟随。忧心常常使他无以排解,断送仅有的一点享受。他希望自己遗忘在酒宴笙歌之中、山水游历之中,可最终仍旧无济于事。他经常为此矛盾、愧疚和不安:“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熙宁中,轼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塞满了囚室的犯人让他难过,为之流下长泪,这些人无知、贫困、绝望,且不知羞耻,对自己可怜而悲惨的处境近乎麻木。“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qī栋。老农释耒lěi 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他当年是不忍看,我们今天是不忍读。
人的心肠只要足够柔软,就会盛满忧伤和绝望,苏东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无法回避,因为职责所在,不能做一个旁观者。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要服务黎民,是一个所谓的“牧者”,羊群有生命之虞,“牧者”就不能垂手而立无动于衷。他的一生留下了那么多文字,从义理皆备、言辞恳切、锋利洞彻的策论、表状、奏议,到无边无际的浪漫抒发,还有那些情趣、机敏和惆怅,一切都掩不住心底的悲叹。他写道:“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读书与实务,思想与现实,就这样差异分明。一个长于作文者,如同一个朝廷里威严的能吏一样,对照苦难的生活现状,常常有一种至为悲伤的痛感:一种空荡无为、苍白可怜的人生感受,油然而生。“轼在钱塘,每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这里记录了他审决案犯的一些心情。面对这些受难者、毫无希望者,他忍不住流下眼泪。这通常不是一个威严官吏的表现,但是毫无办法,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历史上不乏为民请命的文人和官吏,但像苏东坡这样体察下情、疗民之疾、与之情同手足的人实在不多。他之抗争、之辩白、之斗法,都是不忍之心驱动的结果。他不得不以身犯险,冒着极大的危难放手一搏,不计后果,这种莫大的勇气也是以仁心为基、为据、为本。作为一个上层人物,一个名动朝野的天才,却又能如此“接地气”。
我们所见到的苏东坡,其最大魅力其实并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章、那些想象绮丽的文辞,而是与这些文字密不可分的那个灵魂。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有了逼人的力量。那种强大的涤荡力让人久久不能平静,难以忘怀,更超越了一般的审美意义。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