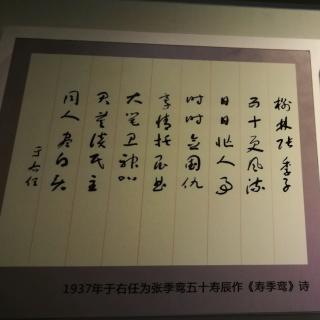
介绍:
《箭术与禅心》第一章
一 禅与日本艺术
初看之下,不管读者是否了解“禅”这个字,把禅与射箭之类的事放在一起,似乎对禅是很大的不敬。就算读者肯退让一步,发现射箭也可被当成一种“艺术”,但若要去探究这项艺术背后所隐藏的意义,而不只把它当成一种运动的表现,读者可能私底下仍会感到勉强。因此读者会希望有人能说明这项日本技艺的奥妙之处。在日本,弓箭的使用是渊源已久、备受尊重的传统。在远东,古老的战斗技能被现代武器所取代还是很近代的事。现在,弓箭的使用没有被荒废,反而更加普及,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扬光大起来。于是难免会有人假设,说不定今日在日本,箭术已经成为一项全国性的运动?
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在日本传统中,箭术是被尊为一项艺术,当成民族的传承的,因此乍听起来奇怪的是,日本人非但不把箭术当成运动,还把它当成一种宗教仪式。所以,在谈到箭术的“艺术性”时,日本人并不认为那是运动者本身的能力,或多或少可由身体的训练来控制;而是一种心灵训练所达到的能力,其目标在于击中心灵上的靶。所以根本上,射手瞄准了自己,甚至会击中自己。
这话听起来无疑令人困惑。读者会说,什么?曾经事关生死的箭术不但没有成为一项运动,反而降级为一种精神练习?那么弓、箭与靶又有什么用呢?这不是否定了古老箭术的阳刚艺术性与诚实的意义,而以一些模糊不清,甚至空幻的概念取而代之吗?但是我们要知道,箭术艺术中的特殊精神自古就与弓箭本身息息相关,非但不需要重新建立与弓箭的关系,现在反而更加明显,大家都相信箭术的精神已不再是为了流血的斗争。但如果说箭术的传统技术已不着重于战斗,而变成一种愉快而无害的消遣,这也是不正确的。
箭术的大道(Great Doctrine)有着极不同的说法。根据大道,射箭仍然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是射手与自身的战斗;这种战斗不是虚假的替代,而是一切外在战斗的基础,包括与一个有形对手的战斗。射手在与自己的战斗中揭示了这项艺术的秘密本质,虽然舍弃了武士斗争的实用目标,但不会降低它的任何实质意义。因此在今日,任何接受这项艺术的人,都能够从它的历史发展中得到无可否认的帮助,使自己对于大道的理解不会被心中隐藏的实际目标所蒙蔽,因为那些实际目标将使对大道的理解几乎成为不可能。从古至今的箭术大师都会同意,要想接近这种艺术,只有那些心境纯净、不为琐碎目标困扰的人才能做得到。
从这个观点,也许有人会问,日本箭术大师们如何理解这种射手与自己的战斗,又如何加以描述呢?他们的回答听起来很玄奥。对他们而言,这项战斗是射手不瞄准自己地瞄准了自己,不击中自己地击中了自己,因此,射手同时成为了瞄准者与目标,射击者与箭靶。或者,用更接近大师心意的说法,就是射手必须克服自我,成为一个不动的中心。然后就会发生最大与最终极的奇迹:艺术成为无艺术,射击成为无射击,没有弓与箭的存在;老师再度成为学生,而大师成为新手,结束即开始,而开始即完成。对东方人而言,这些神秘的道理是清楚而熟悉的真理,但对我们西方人而言,则是无法理解的困惑。因此我们必须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甚至连我们西方人都早已知道,日本的艺术内涵具有共同的根源,那就是佛教。这一点在箭术、绘画、戏剧、茶道、花道及剑道上都是一样的。它们都预设了一种精神境界,然后以各自的方式去达到这种境界。这种境界的最高形式就是佛教的特征,因此具有一种僧侣的本质。
在这里,我不是指一般的佛教,也不是指我们在欧洲经由佛教文献所推论出来的具体的佛教形式。我在这里所要探讨的,是佛教中的禅宗,它完全不是一种推论出来的理论,而是一种直接的体验。正如追求生存意义的无底深渊一般,它是无法用理智来掌握的,一个人只能无意识地知道它;就算是有了这种最明确与肯定的体验,仍然无法加以诠释;为了这些重要的经验,禅宗通过有系统的自我冥思禅定,发展出途径来引导个人在灵魂的最深处觉察到那无可名状的、无根无性的本体——不仅如此,还要与之合一。在此诉之于箭术,以很可能造成误导的言语来形容就是:由于心灵的训练,箭术的技巧变成一项艺术,如果适当地进行,能够成为“无艺之艺”。心灵的训练就是神秘的训练,于是乎箭术就意味着不是外在地使用弓箭,而是内在的自我完成。弓与箭,只是不必要的皮毛,只是达到目标的途径,而不是目标本身;弓与箭只是最后决定性一跃的助力而已。由以上这些来看,最适当的莫过于能直接聆听禅师的说明来帮助理解。
事实上这种机会并不稀少。铃木大拙在他的《禅学丛论》(Essays in Zen Buddhism)中很具体地说明了日本文化与禅宗的密切关系,日本的艺术、武士道的精神、日本的生活方式、道德、美感,甚至日本的知性发展,在某种层面上都受到了禅宗的影响,如果不熟悉禅宗,就无法正确地理解日本。铃木大拙的重要著作及其他日本学者的研究,已引起人们普遍的兴趣。佛教的禅宗诞生于印度,经过了巨大的转变后在中国发展成熟,最后被日本所吸收,成为一种生活中的传统直至今日。一般都承认,禅宗揭示了意想不到的生存之道,这也是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的。
然而,尽管有禅学专家的努力,对于我们欧洲人而言,洞察禅道精义的领悟仍然是很缺乏的。禅道似乎拒绝深入的探究,欧洲人的直觉在初步的努力后,很快便碰上了无法越过的障碍。禅理藏在不可见的黑暗中,就像是东方的精神生活所酝酿出来的奇妙谜语:无法解释而又无可抗拒地吸引人。 这种难以洞悉的痛苦感觉,部分原因要归咎于禅宗所采取的说明方式。一般明理的人都不期待禅师会用超过暗示的方式,来解说那些曾经使他自己解脱与改变的经验,或去描述他以生活所印证的不可思议的“真理”。在这方面,禅宗就像是纯粹的沉潜神秘主义。除非我们直接参与了神秘的经验,否则我们就一直在外面打转,不得其门而入。这是所有真正的神秘主义所遵循的法则,绝无例外。禅宗虽然有许多被视为神圣的经典,但这不构成矛盾。禅宗有特殊的做法,只向那些已经证明自己有资格体验真理的人揭示禅宗的生命真义,因此那些人可以从经文中得到印证,印证一些他们已经拥有,而又独立存在的事物。在另一方面,那些没有体验过的人,即使以最刻苦无己的精神来探求,不仅仍然看不懂字里行间的意义,更会陷入最无助的精神混乱之中。就像所有的神秘主义,禅只能被一个本身已进入神秘的人所理解,而不能用神秘经验之外的方法偷偷去获得。
然而一个被禅所转变的人,通过了“真理之火”的试炼,其生命的表现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于是我们受到心灵的驱使,渴望发现一条道路,通往造成如此奇迹的无名力量。但是仅仅靠着好奇是无用的,我们期望禅师至少能够描述那条道路,这种期望应该不算过分。没有一个玄学或禅的学生能够在一开始就达到自我完美。在他终于洞悉真理之前,有多少事情必须克服与抛弃!他在那条路上,有多少时候要被孤独的感觉所折磨,觉得自己是在尝试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一天,不可能会成为可能,甚至可以自证。那么我们为何不能希望有人能为我们描述一下这条漫长而艰辛的路,让我们至少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走上这条路?
对于这条路及其各阶段的描述,在禅宗的文献中几乎完全找不到。部分是由于禅师都极力反对任何具有形式的指导。禅师从自己的经验中得知,若是缺乏老师的引导与禅师的帮助,没有人能够一直走下去。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由于他的经验、他的克服及精神上的升华,只要仍旧是属于“他的”,就必须不断地再克服与升华,直到一切是“他的”都被消灭了。唯有如此,他才能得到一种基础,让包含一切的真理经验来提升他超越日常个人的生活。他仍然生活着,但活着的已不是他的自我。
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禅师总是避免谈论他自己和他的求道过程。不是因为他认为谈话是不谦虚的,而是因为他把谈话视为对禅的一种背叛。甚至连决定说一些关于禅的事,都会让他感到万分犹疑。他脑海中有一位伟大禅师的例子警告着他,每当有人问那位禅师禅是什么时,他会寂然不动,仿佛没有听到问题似的。如此一来,又有什么禅师会想尝试说明这位伟大禅师置之不理、毫不在意的问题呢? 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我自限于一些谜般的偈语或躲藏在一些响亮的言词之后,我就是在逃避我的责任。我的目标是去说明禅的性质,它如何深入影响了一项艺术。这种说明当然无法解释禅的根本,但是至少要显露有东西是存在于那无法看透的雾中的,就像是夏季风暴欲来前的闪电。理解这一点后,射箭的艺术就像是禅的一所预备学校,它让初学者能通过自己的手而对那些无法理解的事物有一个较清楚的概念。客观说来,从我前面提及的任何一项艺术,都有可能到达禅的境界。
然而我相信,要达成我的目标,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去描述一个箭术学生必须接受的课程。更具体地说,我将要尝试叙述我在日本的六年时间中,跟随一位伟大的箭术老师学习的经过。所以,是我的亲身参与容许我做如此的尝试。即使是预备学校,仍然有许多的谜题,为了使大家都能够理解,我只好详细地回溯我在成功地进入大道之前,必须克服的所有困难、所有障碍。我以自己现身说法,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其他方法来达到我所立下的目标。为了同样的理由,我的报告将只限于最基本的细节,这样可使它们更清楚明白。我刻意避免描述这些教诲的背景环境,以及深深刻印在我回忆中的情景,以及最重要的,避免描述师父的形象——虽然这是非常难以克服的欲望。我要描述的一切都环绕着箭术,而有时候我觉得箭术的说明比学习还困难;这些说明必须够深入,让我们能瞥见在遥远的天际,禅所活生生存在并呼吸着的空间。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