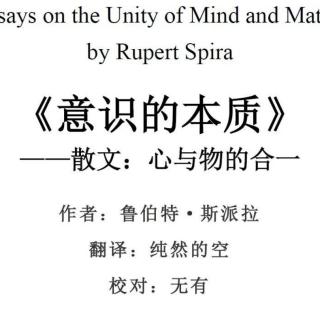
介绍:
第18章
寻找快乐
(续)
事实上,并不是人类渴望快乐。人类的体验是心念之流,即一系列体验——从集体和个人“无意识”的潜意识状态,到清醒状态下更明确和更集中的形式。每一颗心都是一条能量的脉动之流,通过它并作为它,觉知实现了它无限可能性的一部分,因此,心是觉知本身的部分现实化。个人化的心是媒介,通过它,觉知似乎变成了独立的体验主体,从这个角度,它能够认知客体化体验。因此,二元性是创造的机制。
不过,觉知的这种部分现实化涉及到一个交易——觉知必须同意自我限制,以便将其无限潜力的一个片段现实化。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它允许自己无名无形的存在采用名称与形式。经过这一同意,无形的存在呈现为有形的存在。为了将显现(现象界)从无形存在中带出,进入有形存在,无限必须压缩为有限。由这种压缩而产生的张力,就是对快乐的渴望。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快乐是其为自己而渴望的东西。个人很少认识到,对快乐的渴望只是一种平衡力,为的是放松或消除这种张力,这张力是对觉知的局限中所固有的,并从觉知中诞生了它的表面存在。个人什么都没有做,个人甚至不拥有属于其自身的状态。个人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个实体。
表面独立自我或有限之心,及其所感知到的世界,这整个存在都是存在于觉知中的、觉知的游戏。觉知本身以牺牲自己内在所固有的快乐为代价,让世界进入表面存在。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它似乎与自身造物的方方面面融合得如此密切,以至于在其中迷失了自己,然后,当它消除了自我假设的局限,回归自身时,它又重新获得快乐。这就好像,觉知在呼气时把独立自我从自己之中呼出,紧接着是自然的、吸气的冲动。
当我们的真实本性在它自己的想像中自我迷失时,对快乐的渴望,是它对自身的引力。来自我们真实本性的引力,是完全自由且内在满足的觉知对有限之心的牵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引力被感受为欲望或渴望。不过,这个说法是对表面个人的一种妥协,从个人想像中的角度来看,它似乎拥有自己的独立存在性。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独立自我的存在,因此,不存在这样一个自我回归其真实本性的问题。
正是由于在电影中屏幕无处不在,所以,它不可能呈现为电影中的特定客体,因此,从电影中人物的角度来看,屏幕似乎失落在了电影中,从而似乎不见了。类似地,正是由于觉知是如此密切且均匀地弥漫于一切体验之中,所以,它永远不可能变成体验的特定客体,如此,从表面独立自我或有限之心的角度——体验被认知的角度——来看,觉知似乎不见了。
觉知只是看上去不见了,因为它是如此完全地存在于其造物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无法与之区分开。从它自己的角度来看,觉知中没有任何不同于觉知本身的东西,因此,不存在体验到其自身缺失的问题。觉知似乎不在,因为它无处不在。它似乎什么都不是,因为它是一切。
一旦觉知通过自愿采用身体的局限而在表面上自我遮蔽,它就似乎切掉了对自身内在平静与快乐的认知。所以,表面上的独立自我感到自己的心中受伤了——某种东西找不到或丢失的感觉(或若有所失的感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约翰·班杨(John Bunyan)说,上帝通过伤口进入灵魂。这个创伤引发了对快乐的追求,这是独立自我的典型特征。
独立自我不是实体;它正是这追求的活动。独立自我,没有感觉到这创伤;它就是这创伤。不是自我在向上帝前进;正是上帝在吸引自我。自我朝向快乐前进被称为欲望;快乐对自我的引力被称为恩典。正如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修士所领悟的那样:“上主,您就是我用来爱您的爱本身。”
当个人认识到,它的整个体验一直都倾向于回归其自然状态时,它就会意识到,它什么都没有做。对快乐的渴望,仅仅是它对上帝的回应,上帝邀请它回归;对快乐的渴望,是恩典,是觉知对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引力——当觉知似乎已经忘记或忽视其真实本性时。
在独立自我或有限之心的一生中,反复产生的、回归其自然状态的冲动,可以被一个客体、一个人或一种教导所引发,该教导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有限之心消融,回归其无限源头,这种冲动也可能发生在许多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在每一个念头或感知结束时,在每一天结束时,以及在每一世生命结束时。
***
早在我能够清楚地表达这一点之前,我就有了第一个关于此的直觉,正如大多数人一样,尽管这种直觉常常因为缺乏适当的指导而被忽视。在第五章描述的学校危机发生几年后,我发现自己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博德明(Bodmin)荒原边上做学徒,师从于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工作室陶艺运动(studiopottery movement)创始人之一。迈克尔·卡杜(Michael Cardew)是一位老禅师,一方面脾气暴躁,另一方面热情又善良。再加上他冷酷无情的聪明才智,这使他成为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对于一个年轻的、在他所受教育能够提供的范围之外寻找意义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无法抗拒的邀请。
然而,这是有代价的——在博德明荒原边上的生活是孤独和清苦的,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朋友的安慰,也许是无法忍受的。但我有一个朋友。每周五晚上,晚餐后,我都会沿着小路走一英里左右到村子里,然后,在电话亭里给她打电话,电话亭坐落于穿过荒原的道路交叉口的一块三角形草地上。那个星期五晚上,像以前的许多天一样,我走到电话亭寻求庇护。我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包含在她的问候中。之后,我什么也没听到。
就在我走下山的时候,我直觉地意识到,几年前,我在学校里遇到的困境,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维度,而且即将加剧。关于心的哪一方面知识是可靠的这个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兴趣;它一直困扰着我。这不再仅仅是关于知识的问题,而是关于快乐。当这个问题在我心中被理性化之前,我感觉它仿佛在我的身体里燃烧。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我对吠檀多教导的探究,作为一名艺术家,在我的工作室里寻找美,以及在亲密关系中寻求幸福和爱,都是同样的探寻。
这场燃烧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探究——关于快乐的本质、它的源头,以及能够获得它的方法。如果某人或某物可以一时成为快乐的源头,一时成为痛苦的源头,那么,一个人可以将对快乐的渴望可靠地投资于什么呢?在那次简短的电话中,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得到了一份最伟大的礼物: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找到持久的、无条件快乐的本质及其源头。
从理论上讲,只有这样一种体验可以清楚地表明,造成内心创伤的原因不是缺失任何客体、状态或关系,而是忘记、无视或忽视了我们永恒存在的、无限意识的本质,其本质就是平静与快乐。但在实践中,我们大多数人都需要在失败的关系、不幸、幻灭或失望中进行许多次这样的启示,才能认识到这一点。
大家还在听

